
袁宝林:中西之间——司徒安的启示
2017-04-20 11:53:43 袁宝林

司徒安《莎士比亚胸像》铸铜 860×300×500厘米,2008
在中国美术馆的后院园地,一座巨大的莎士比亚胸像(铸铜,860×300×500厘米,2008年)静静坐落在洒满阳光的梧桐树边。这是曾担任英国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的著名艺术家司徒安(Anthony Stones,1934—2016)的作品。他是西方古典雕塑的传承者,而从那似乎泥土尚未干透的颤动着的塑造手法中,我们即刻感到他实在是罗丹以来的印象主义和浪漫派的注重表现的艺术家——难怪他自己说,“我是为粘土而生。”这里还陈列着他临摹放大的那件出土于维也纳的“威伦多夫的维纳斯”,他为之冠名《世界第一女神》,可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现着他对欧洲传统源头的尊重和对艺术要义的理解。
这个主题为“中西之间”的司徒安雕塑绘画艺术展是一次重要的国际艺术交流展,它以美术馆三个展厅(西厅、西南、西北厅)加室外园地壮观宏大的规模展现出这位精力旺盛的艺术家对历史和当代生活的非凡热情与敏锐感触;特别是,我们十分欣赏和珍视他在晚年与中国文化的密切接触中为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里,笔者就想着重从两个方面谈谈司徒安的艺术给我们的启示。

司徒安照
异中之同——共同的艺术趋势
司徒安的艺术从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更重情感表达的表现主义特征;这一点和我国当代艺术近年来更看重写意传统的总体趋势不谋而合。在司徒安,这不仅表现在他所钟爱的经典题材——例如从莎翁到堂·吉诃德——素材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和浪漫情调;从他近年在中国创作的如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吴冠中、吴为山等塑像看,也突出地表现出一种选择性:无论中国传统派大师,还是更多借鉴西方的画家、雕塑家,都是“写意”型,或说重于“表现”的艺术家。这也清楚表现出司徒安的主观情趣与好尚。

司徒安 堂·吉诃德夜遇汉代马车 纸本水墨 68×135厘米 1984
在绘画创作中更有一个有趣的例证:在美术馆西厅北墙面的显著位置,并排悬挂着司徒安的四幅作品:一幅骑马的《堂·吉诃德》,另三幅题目分别是《堂·吉诃德巧遇汉代马车》(纸本水墨,92×97厘米,1984年)、《堂·吉诃德夜遇汉代马车》(纸本水墨,68×135厘米,1984年)、《堂·吉诃德晨遇汉代马车》(纸本水墨,67×133厘米,1984年)。1984年他第一次来中国,而就在这一年,几乎就是他艺术生命化身的堂·吉诃德与汉画像石上的飞奔着的马车撞了个满怀。真是不期而遇!他用的画题不就是要表达自己处在一种朝思暮想的痴迷状态吗!汉画像石上那夸张而富有装饰意趣的车马形象被他用一种流畅和富有东方韵味的水墨与线条律动反反复复地表现着。在这里,他以戏剧性的独特幽默方式,用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惊愕作为陪衬,以此表达他与东方艺术相撞击那种极度兴奋的心情。他对东方艺术的热爱与强烈共鸣不是偶然的,这一点他的夫人冯莉莉女士有最真切的体会。她说,为了更多和深入地研究中国艺术传统,他竟然三次去麦积山考察。展出中还有一件水墨速写《心有灵犀》,以流畅而富于变化的线条,生动展示了他对东方艺术的精神性把握和对东方意趣的浓厚兴致。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为此次展出所写序言中这样写道:“一个年逾七十岁的西方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文化时竟晚年变法,试图远离客观形体结构的科学塑造的母语,直追形而上的东方造型之美。”这并不是夸张。

司徒安 曹雪芹 铸铜 33×27×60厘米 2007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东西方艺术所表现出的这种共同趋势,实际上是从19世纪后半叶,大体上从后印象派开始,伴随西方艺术进入现代阶段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正如陈师曾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文人画之价值》(1922年)中所说:“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再看西方两位著名的美术史家是怎样描述这一重要变化的:

司徒安 黄宾虹 铸铜 48×22×10厘米 2008
西欧的表现自然的传统是建立在扎根于科学之中的技术基础之上……20世纪的艺术,主要是面对照相技术这个可怕的敌手的艺术,可以说是与上述传统的方法完全相反的东西。然而人们把目光转向远东的伟大艺术,也正好就是这个时代。(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日文版序言)
(现代艺术)虽有其复杂性,但也具有一个统一的倾向,使它和以往的绘画迥然不同……这个倾向就是不去反映物质世界,而去表现精神世界。(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序)

司徒安 苏立文 铸铜 61×17×45厘米 2008
很明显,这里反映出陈师曾先生一方面熟稔中国传统,并对本民族优秀艺术传统充满自豪,一方面又是站在世界艺术发展的前沿,在同一文化语境中与西方的对话。而就中国传统而言,如我们所熟知的唐代张璪论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国画的写意传统,不仅发端于对外界自然的认知,更是看重主观心灵的感受。而受到明代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推动,特别是反映在文学艺术上“性灵派”的崛起,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人写意传统,就尤其突出地表现出一种更重视表达艺术家主观情怀和更强调精神活动能动性的时代风气。当与西方历来以“反映物质世界”为特色的古典写实传统相遇时,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如以齐、黄、林、吴等为代表的上述司徒安所喜爱的艺术家与西方艺术的迥乎异趣了!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恰恰是与照相机的发明所显示的机械功能相悖谬的方向;可以说,是东西方艺术的戏剧性相会,共同促成并推动着对艺术本质特征认识的觉醒和提升。

司徒安 贝多芬 铸铜 42×51×94厘米 2008
同中之异——写意与写实的互补
如果将东西方艺术传统做一对照,西方艺术无疑是更偏向于写实的;从西方美术的发展历史来看,尽管它有一段(中世纪)“表现主义”的异军突起,其自希腊、罗马以来所奠定的古典传统基础——也是它的突出优势则是具象写实。这在司徒安的作品中仍是表现得如此明显和突出。他的大量肖像作品所表现出的驾轻就熟的能力及其丰富性、生动性,都充分展示着西方造型艺术的这一传统特色和优势。

司徒安 中国情缘之五 纸本水彩 29×40厘米 1984
恰逢莎士比亚——同时也是中国戏剧大师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之际,当看到司徒安那样多从巨大体量到青年时代莎士比亚丰富多彩的各种变体塑像时,我不禁在想,我们的雕塑家不是也应当创作几件伟大中国戏剧家的塑像吗?然而不必讳言,当我们做这样设想时,立刻就会意识到,虽则我们的传统历来讲究形象表现的“传神阿堵”,但就整体的写实能力而言,譬如与古代罗马的个性化雕塑相比较,却就暴露出无论绘画还是雕塑,在我们的历代作品中,几乎找不出像西方古代作品中那样多具有肖像特征的历史人物的生动确凿形象。

司徒安 15世纪的住宅 纸本水彩 56×76厘米 1984
在20世纪初中国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一个可能被我们轻易地忽视了的艺术史实,即是由康有为振聋发聩地发出了从我们自身传统(所谓“以复古为更新”)特别是从西方引进写实绘画的呼吁;而徐悲鸿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巨大变革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开山地位,其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也正在于他从理念到实践成功地将西方的写实主义传统,尤其是严格的人物写实引入到中国,从而成为康翁所说“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英绝之士”!我们还有一个误解,即当西方以迅猛的步伐,甚至被形容为“大河改道”之势的由写实而转向“写意”时,我们却是逆向而行——由“写意”而转向了写实——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东西方艺术的互补;应当说,这样的现象刚好出现在艺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节点,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但从中国美术的总体发展趋势看,这其实只是对我们传统一个必要和重要的补充,而并不是我们改变了方向——这一点我们今天会更加清醒也看得更清楚。

司徒安 世界的堂·吉诃德 纸本油彩 50×40厘米 1984
这里用得上悲鸿先生在谈到关于传统与素描关系时的一段话:“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但所谓造化为师者,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而诬注重素描便会像郎世宁或日本画者,仍是一套摹仿古人之成见。”(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1947年)在这里,徐悲鸿十分精辟地指出了,“直接师法造化”,乃是使艺术家的创造和自然万物从视觉形象的意义上保持最生动的此在性联系的根本途径,它是要从根本上打破包括“郎世宁或日本画”模式在内的一切摹仿古人或他人的成见和套路,而真正打通并开辟出一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正确创作道路。这就引出了我们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应有的新的认识,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进写实方法,实是改进与提高、落实和兑现“外师造化”的重要手段和保证。然而“仅直接师法造化”却并不是我们对继承传统精华的认识的全部,而是,进一步的认识更在于通过师法造化,而达到“中得心源”的更高境界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悲鸿先生更以做出实绩的当代画家作为范例,举出如他本人和叶浅予、蒋兆和等大家的作品,强调指出“中国画可开展之途径甚多,有待于豪杰之士发扬光大”。这样富有实践意味的展望,甚至足足超出本人必不可免的历史局限,无疑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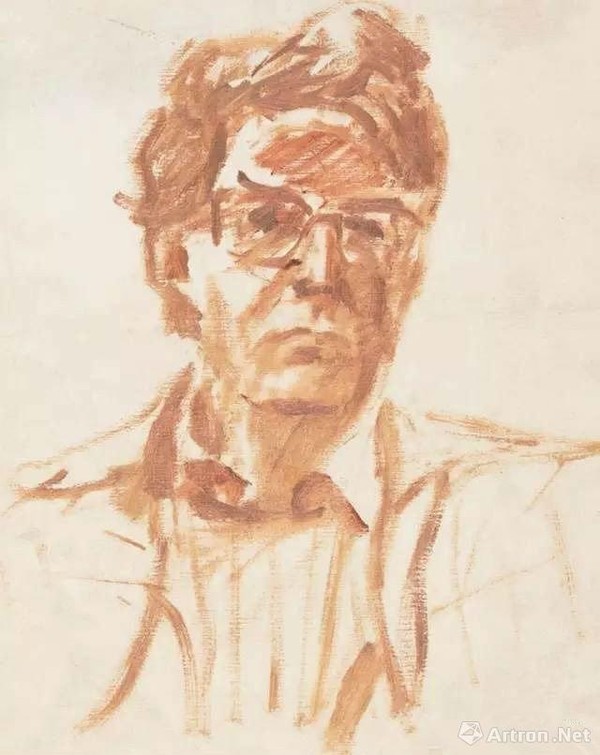
司徒安 永远的司徒安 纸本水彩 51×40厘米 20世纪90年代
再回到由司徒安西方式的“写意”给我们的启示吧:如果说我们对写意的理解,是可以比喻作“放开”,那么,苏东坡的一句诗:“始知真放在精微”,则刚好可以说明,从历史到现实,我们缺少和有待补充的,却正是以写实为基础的、把握“精微”的能力。相对地看,这一点在我们不是已经掌握到出神入化,而是依旧有更大施展的空间。

司徒安 吴为山 铸铜
司徒安与吴为山的相遇与对话
促成这个重要展览的实现,我们应当特别感谢司徒安的中国妻子冯莉莉女士和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先生。这位有着爱尔兰、英国和新西兰三国国籍的已故杰出艺术家在他的生平自述中曾说:“我哪里会想到60岁后我会有一个优秀的中国妻子,哪里会想到这个神秘的国家成了我的第三故乡!”他追述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关注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和国家”而由于和中国的亲缘关系更使他无比热爱中国文化并具有深厚的中国情结。有趣的是,雕塑家吴为山刚好是一位长于写意而十分看重如何能传达出中国神韵又有很好写实基础的当今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我们从吴为山为此次展览所撰写的序言中得知,吴为山曾于2003年在他担任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所长期间,就曾邀请司徒安到访,而他们的初识便是以对塑开始,这又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东西方艺术家的相遇,可说两方面同样“心有灵犀”。如今在南京博物院还保留着此间司徒安与吴为山分别创作的两件雕塑——司徒安作的是米开朗基罗,而吴为山作的是齐白石——从不同的意义上说,两者都是写意性的。当然,我们相信,两位艺术家的对话并非偶然的邂逅,而是真实地具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
(责任编辑:杨晓萌)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张瀚文:以物质媒介具象化精神世界
张瀚文:以物质媒介具象化精神世界 吕晓:北京画院两个中心十年 跨学科带来齐白石研究新突破
吕晓:北京画院两个中心十年 跨学科带来齐白石研究新突破 OCAT上海馆:参与构建上海艺术生态的十年
OCAT上海馆:参与构建上海艺术生态的十年 一级文物逾半数!部分仅展20天!辽博秋季大展聚焦古代文人的园中雅趣
一级文物逾半数!部分仅展20天!辽博秋季大展聚焦古代文人的园中雅趣
全部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