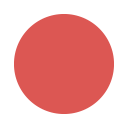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创作是一个日常的生活,不论是在何种时代背景下。我一直是一个喜欢宅的人,所以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转眼已宅了一个多月了,一次门也没出去过,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安,每天照常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不刻意要求自己在隔离期一定要做出一些有实效意义的作品来。只是见不到朋友了,大家都只能在微信上交流,更多的时间是与自己对话。
每天网络上都是各种分不清真假的信息狂轰滥炸,也为许多充满悲剧的事件动情,恐惧,愤怒,绝望落泪,但更多的是某种无奈和无能为力的感觉。这些也许会直接影响到近期的创作,也许只是停留在对现实和时代的体验观望中,不知道,也许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一切。这一月来,虽然沒有身处于疫情的中心,但我与许多人一样深刻的体验到病毒的无情同时也导出了人性的某种恶毒残暴,这种交织在一起的恐怖,会自然而然地尤其被那些朴素单纯的情感深深感动。疫情终会过去,但人性之恶已成某种毒瘤深植于我们心中,只要机会成熟它们就会被激活迅速吞噬掉灵魂,使之腐烂发臭,永无解药,这才是最令人恐怖的病毒。我知道自己不具备将现实事件迅速转化成作品的能力,无法直接上升至观念的形而上层面去指导自己的创作方向,我也不具备在本体论的研究中超越现实生活影响的能力,但之后会看到每次大时代降临时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某些烙印,这些烙印日积月累便会形成某种摆脱不了的情感形式,不论你是去画一张脸一把椅子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灯泡,它们都似乎被魔鬼附了身一样,成为某种魔幻的组合,永远存在,不那样去画心里就会不安,就会觉得那只是一具空壳。我不会为时代去创作,我们的历史曾不止一次的告诫我们要去表现时代,去塑造伟大开拓未来,但往往却使艺术沦为了欺骗的工具。我开始怀疑艺术究竟能否改变现实一如果它连面对自己的真诚和勇气都没有的话。大时代小时代好时代坏时代都是某种体验,都会激发艺术的思考,都是我们可以获取和运用的资源。我相信人性的复杂和矛盾的魔力,从中我可以体验到善与恶,美与丑,真实与谎言是如何相处又互为转换的,在几十年的风雨跌砳中我不会再去相信所谓的绝对真理,就如对明天的期望实际上不过是基于对过去的某种神化和意淫一样。艺术就是与自己相处与“神”对话的某种日常,在某种自在的生命状态中,才能更为专注和深入,使作品不至沦为某种失血,徒然劳作急功近利只会生产出一个简单的符号,一具仅仅是有标签意义的躯壳。我始终记着卡夫卡在一百多年前曾说过的一句话:“人不是从下往上的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的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
张晓刚,《镜子2号》(Mirror No.2),2018张晓刚,《跳跃1号》(Jump No.1),2018
纸本油画、纸张拼贴,194 × 86cm
张晓刚的艺术中暗藏着一片“遗忘”之所,它是创造力嬉戏的所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遗忘、“我”与“非我”一同在这里汇聚。艺术家解除了我们身上的枷锁,让我们能够自由享受幻觉带来的欢愉,同这幻觉成为完整的一体,而不再是将之驱散并代之以过分坚硬的“真实”与“现在”。张晓刚用他的绘画为我们展现了过去所蕴含的丰富养分,让我们自信能够在经验断裂之处承受完全的孤独。在这里,我们同自己的个体性重逢,在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与之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张晓刚 (蔡小川 摄)
生于1958年,是最早为海外所认识和熟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被栗宪庭评价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缩影式艺术家”。他将来自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社会、集体记忆和私人回忆的典型意象予以抒情性和高度自由的提炼、重组、并置和更新,将一代人历史经验普遍化的同时又赋予其全新的生命力。张晓刚的艺术不仅仅是属于中国人的艺术,面对亚洲世界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撕裂和阵痛,来自历史、文化、传统、记忆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正是整个亚洲所需面对和承担的,而这同时也是整个全球化社会中在地性的一次重要展演和叙述。

【 惠书文|艺评 】朱峰 · 20年代:雕于气,塑之以息的“数字装置”
This article is published by exclusive AN-ART SPACE, the artist authorized to publish, without permission, please do not reprint.DIGITALl MEDIA OPERATION PLATFORM
Copyright © 2020 AN ART SPACE. All rights reserved.Learn More About Art InformationCopyright © 2020 AN ART SPACE.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中国当代艺术
特别声明:本文为艺术头条自媒体平台“艺术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艺术头条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