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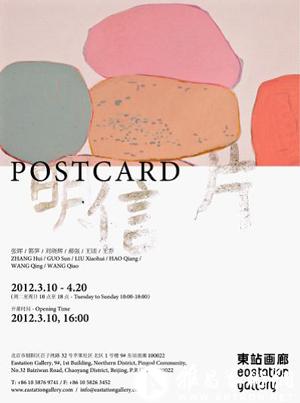
玉光集| 常玉:我不是梵高

这句话不是常玉说的,是我想要说的,很多人提起常玉,梵高等画家,第一反应就是:缺了的耳朵、精神病患者、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平庸一辈子、拍卖会上的天价、死后才出名……等等。
这是无知并浅薄的认知,无论是对艺术家,还是对艺术本身,都是十分片面的主观看法,这种世俗的优越感并不能让人感到学识的渊博和对艺术的了解,最基本的敬畏也没有。

常玉,原名常有书,1900年10月14日生于四川顺庆(南充市)的富商家庭,1910年即与赵熙习画,长于书法的他,1917年入上海美术学校就读,1919年常玉与徐悲鸿、林风眠以留法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巴黎,并于1919年赴日时在东京展出其书法作品,而获当地杂志刊载推荐。常玉自20岁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到巴黎,1921年与徐悲鸿、张道藩等留法学生组织“天狗会”。至67岁辞世,大致都住在巴黎。此后,他的作品经常在沙龙及各大画廊展出。1938年他曾短期回中国,接着转往纽约,在该地生活了两年。并于1948年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作品。该馆同时印行“瓶花”的彩色明信片。1948年返回法国,直至1966年逝世于巴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常玉40几幅油画巨作,曾于1978起定期举办他的回顾展及学术研究,藉此宣扬他有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成就……

这段简历,并不是一个所谓郁郁不得志的人会拥有的简历,常玉在法国时已经小有名气,他与梵高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性格,性格决定了他们做出的选择不同,以至于命运并不相同,梵高郁郁寡欢是因为他的风格不被人所认可,导致他在生前没有名气,他拿自己的画送给咖啡馆人家都不要,而常玉,结合他的家庭环境和他所处的艺术氛围,造就他的性格孤傲清高,并且十分注重自由与追求,他主动选择了这样的人生,且并不后悔。

常玉就像是古龙小说里的浪荡侠客,由于早年跟随著名书法大家赵熙学习书画,他的笔触里自始至终都带着一股似有若无的文人气,常玉在当时的巴黎,可谓是独树一帜的不跟风,不随波逐流,做着‘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他的画中,无论是人像,还是动物,植物,都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质朴和天真,颜色与线条的表达之中蕴含着纯粹的真诚,不矫揉造作,也不堆砌繁琐,仅仅是最单纯的表达,干净,透亮,自由,无拘无束,然后还有他内心里,同样干净纯粹的一份孤独。时常让我想起那些独自仗剑行走江湖的浪荡侠客,有酒喝酒,有肉吃肉,活得恣意,自我,他的笔是他的剑,他唯一拥有的物质上最能满足他的东西,他是非常柔软的,体现在他的暖色调里,他的线条里,他的孤独里。有不少人把常玉比作贾宝玉,都是富贵大宅门里养出来心思至纯的公子哥,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人事物,始终没有丢掉这份稚纯的心性,倔强地活得干干净净,白茫茫一片,无拘无束。
常玉曾经说过: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
黄永玉在书里讲过一件关于常玉的趣事:五十年代初,中国文化艺术团来巴黎,访问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那时候常玉五十多岁,已经过了声名鹊起的时期,受访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二者相识。
代表团中有位画家劝他回国,还可以做个美术学院的教授,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住在暖气不足的阁楼,靠一年卖两三张小画勉强维生。常玉只回答说:可是我早上起不来床,也做不了早操…… 这样的理由可谓不算理由。
再早几年,吴冠中对常玉有更为直观的第一印象,“当时在巴黎男人很少穿红衬衣,他显得很自在,不拘礼节,随随便便……他说哪儿舒适就呆在哪儿……给我的印象是居无定处的浪子。”
黄永玉用《世说新语》里的一个句子总结他:“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句话出自东晋名士殷浩之口。魏晋之风清朗陶然,那个年代,既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又有竹林七贤吞石服药而不入世的狂放。形容常玉其人,其作品,恰如其分。
早在 1925 年,常玉的作品便入选秋季沙龙。又在 1932 年被列入《1910- 1930 当代艺术家生平辞典》。如此发展下去,功名利禄都将接踵而来。但是常玉对这一切都毫不在乎。
他常常把画送人,也不愿出售。他跟请他画画的人约法三章:一是先付钱,二是画的时候不许看,三是画完拿走不提意见。这一方面是因为常玉个性随心所欲,一方面也是不满于当时画商对艺术家的垄断和打压的经营方式。
一如常玉在绘画中的追求,无论是初到巴黎时进入与学院派背道而驰的“大茅屋画院”;小有名气后不屑于画商合作,挥霍无度又沉溺美色间“浪荡子”形象;亦或是晚年穷困潦倒,在彷徨和无助中客死他乡的唏嘘结尾,都用浓厚的传奇色彩,满足了社会对一个“梵高式”悲剧艺术家形象的所有想象。然而想象终归是想象,艺术的天赋与他家境殷实的熏陶,是无法磨灭的,不是每一个画家都能承受得起世人无尽的评判和鉴赏,也不是每一个画家都能够承受得住拍卖会上的天价,上一个达到这个高度的是毕加索,然后是赵无极,随后是常玉。

谁的光明又能比谁的黑暗更可贵?显然这是无解的问题,常玉不是为大家解答疑难的艺术家,也不是为了要和所有人发出共鸣的艺术家,他只是他自己,完完全全地,纯粹地,自由地做了一辈子自己。
业界常言,一个画家能否成名,除了本身独特、杰出的艺术造诣不可或缺之外,需要有背后三种力量的支撑:一是美术馆、博物馆在学术专业的认同;一是画廊、经纪人或拍卖行在艺术市场的举荐;另一则是收藏家的青睐与购藏。而如今常玉的广受追捧,便得益于这三方力量的协作。裸女、花卉和野兽是常玉作品中的三大主题。纵观近十年来常玉作品在拍卖行的成绩,多数都以八位数高价成交。2011 年,他的《五裸女》由罗芙奥拍卖公司在香港拍出1.28亿港币(约合人民币1.07亿元),刷新了华人油画的最高成交价。
1959年,常玉生前重要赞助人知名作家侯謝(Henri-Pierre Roché)逝世后,其遗孀在跳蚤市场抛售常玉作品,被慧眼识珠的巴黎画廊尚‧克劳德‧希耶戴(Jean-Claude Riedel)的买下,为后来常玉市场的崛起埋下伏笔。1964年常玉应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之邀计划在台任教,寄出42张油画抵台。没想到尚未抵台,他就在1966年客死巴黎,这批画终被划归台湾历史博物馆接收,后来成为常玉晚期画作最完整的收藏。
林天民回忆,在大未来画廊的创业初期,他和耿桂英经手过上百张常玉油画,但担心常玉作品流散出去,均只加微薄的利润便快速转售给华人藏家,至今常常引以为遗憾。“经营常玉很大的困难在于,第一必需抑制价格过度向上扬升,第二是阻止巴黎的画外流到别处,因为拍卖公司也开始跟巴黎藏家买画;第三是又要增加价值以提升藏家认同感和市场信心。一直到常玉几乎所有作品都到了华人藏家的手上时,常玉才真正开始在拍场爆出天价,这个经营布局整整有十年。”
试想,如果梵高在生前也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也许梵高不会是今天的梵高。
常玉假如知道他今天被人赞颂为“中国的马蒂斯”,“身价最高的华人画家” 等等的称号和标签,恐怕也只会一笑了之,他如流水,我行我素,无拘无束,干净透彻,流向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他能做他自己,他也只能做他自己,某种角度而言,他确实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常玉不是梵高,他是他自己,他是常玉。
更多艺术品拍卖信息:
wechat:blakeyshot
13148807271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