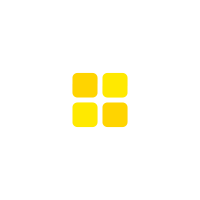实际情况是,尽管他说过这样的话,贾科梅蒂仍然是一位现代派艺术家。他是还原论者(reductionist),与蒙德里安不无相似——尽管有差异——既非优雅亦非狂躁。蒙德里安与贾科梅蒂两人各自发展了一派多样又简朴的造型套路,以有序反对杂乱无章;两者之间唯一的共性就是那种简朴之风。蒙德里安将画面删减到只剩下格子,贾科梅蒂则把雕塑简化到最后只剩下一根棒子,并且像雕刻家刻石头那样运用黏土,不是照传统的工艺手法那样往上堆加,而是,往外挖取,直到几乎孑然无余,只有骨架、骨骼,一个饥饿的隐喻。贾科梅蒂的那些作品——被纵向拉伸得又瘦又长、铁丝般细长的人像;线条纵横交错状如网格的无色油画;以及再后来笔触潦草形同涂鸦的静物素描——竟然能博得满堂喝彩,的确令人讶异。若说他早期的立体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作品能博得这般彩声倒还好理解;贾科梅蒂自己形容它们是“我所能抵达的最接近我的真实视象的位置”,例如《汤勺妇人》(The Spoon Woman,1926年),《被割了喉咙的女人》(Woman with Her Throat Cut,1932年)、《清晨四点时的宫殿》(The Palace at 4 am,1932-1933年)或《隐形》(Invisible Object,1934-1935年)。

这些作品正符合当时的时代风尚和精神。事实上,它们是立足于含混朦胧的表意方式之上的,特别依赖它们的标题,含混朦胧是它们迷人力量的关键。附上一个标题就好比是汉字有了“偏旁部首”,从而决定了符号的意义。(不过,克利的作品也确实被他自己冠以各种标题,从而带上了一层诗意;也正由于这个缘故,超现实主义者们硬说他是“自己人”。米罗也是如此)。超现实主义者们把文学的或“诗意的”趣事秘闻带回到视觉艺术之中,哪怕被抹上非理性的色彩也在所不惜。他们特别偏爱异常清晰的昔日轶事,因此,作品的标题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没了标题,我们还会被《清晨四点时的宫殿》所吸引吗?作品的神秘动人之处全在于标题,而非形式。如果没有了标题,《被割了喉咙的女人》还不就是一堆难懂的跟螃蟹似的东西吗?还会像画的对象吗?

另有一些同时代的艺术作品也是如此,例如尤里奥·冈萨雷斯(Julio Gonzales)的《头发》(Hair,1930年)、《Danseuse a la Palette》(1933年),或者布朗库希(Brancusi)的《鸿蒙初辟》(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1924年)、《帕格妮小姐》(Mademoiselle Pagany,1920年)。这类作品是象征形式的精华,贾科梅蒂也加以运用。原名《Tete d'Homme》[1]的《头盖骨》(Head Skull,1934年)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是模仿原始派艺术风格(例如《汤勺妇人》或《两口子》)呢?还是采用象征形式(例如《被割了喉咙的女人》?贾科梅蒂在1926-1935年间的雕塑作品一直在两者之间徘徊。实质上这些作品与其说是雕塑倒不如说就是物体,但却是富有魔力的物体,它们指示的是想象的主题,而不是实际看到的主题。关于这一时期的创作,贾科梅蒂后来曾有文字叙述:“我所感兴趣的不再是外在形式,而是我自己究竟感觉到了什么”。[2]

贾科梅蒂后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不过1935年以后他不再采用诗意性的标题,而且那些无名的头像和人像的外在形式也完全内在化了,例如《狗》(The Dog,1951年)、《行人》(Walking Man,1960年)或者《一个男人的半身像》(即迭戈)(Bust of a Man,1965年)。在其内在形式的压力作用之下,贾科梅蒂火山喷涌似地创作了大量雕塑作品。与他的素描和油画作品不同的是,这些雕塑作品并非真正根据写生做出来的。他反复地用似是而非的方式提出“相似性”的问题:“要复制出一个人所看到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事”。[3]之前他还说过,要是让他在一幅拉斐尔画的肖像、丢勒画的肖像与一帧福煦将军(Mashal Foch)的照片之间选择,他更偏向于后者。他还谈到自己的雕塑作品《狗》(1951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中总有一个印象,那是一条中国狗,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的。然后有一天沿着德范维街在雨中漫步,我紧挨着街边的楼墙走着,感到有些伤感,也许那会儿感到自己像一条狗。于是我做了这件雕塑;但它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东西的相似物……不管怎么说,芸芸众生们自己才是唯一的相似物。我永远也看不厌人。如果我去卢浮宫时不看画或者雕塑,而只是看那里的人,那我就压根儿不能看艺术品,只得离开”。[4]

贾科梅蒂从而意识到一个事实:“相似性”是无法靠记忆来创造的。可他仍在凭借记忆进行着创作,这与他的倾向完全相悖:他非常倾向于根据写生来创作,倾向于摆脱一切中介手段、从眼前的某张面容中而不是从记忆中来撷取这张面容真正的“相似物”。这就好像果子是从树上、而不是从罐头里采下来的一样。贾科梅蒂一再尝试,一再失败。他一直挂在嘴边的是“我推倒重来”(Je recommence tout),而不是说“你好”(hello)。就像伦勃朗当年的做法——按约阿希姆·范·桑德兰(Joachim von Sandart)的说法——贾科梅蒂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做着同一个头像:那三座堪称青铜雕塑的杰作系列半身像《埃里·洛塔》(Elie Lotar,1965年)即可为证。
当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放弃了在雕塑人像的过程中运用象征形式、并度过了茫然无措的一周之后,他说:“……我要从做一个头像开始”。[5]人们常引用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的话(参见《源于观察的素描》一章)[6]说:“人人都知道一个头是怎么回事”。[7]但他其实说错了:并没有哪两个头颅是一样的,把一个做像了对于做另一个可并不管用。相反地,艺术家必须竭力排除前一个头像在他脑海里留下的痕迹,方能牢牢抓住他此刻正在塑造的头像的特征。布勒东不会明白这个道理,他学识渊博,但对绘画艺术的特性毕竟还是个门外汉,尽管他对绘画也非常痴迷,对绘画作品的主题也颇有见地。他讨厌塞尚,对马蒂斯也没有好感;他对绘画艺术的好恶深受超现实主义实验的影响。贾科梅蒂也曾在1930-1935年间一度浸淫这种实验中,但后来退了出来;当时有报道称他在退出该阵营时曾对布勒东说过这样一句话:“迄今为止,我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手淫!”[8]接着德朗这个先例,贾科梅蒂回归到视觉的源头,将眼睛的看与手的动作、手的动作与内心的感觉重新联系起来。但他始终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信徒,坚信当代艺术是不可能再回到大卫(David)或者安格尔(Ingres)的时代了。然而在贾科梅蒂心目当中,奇马布埃(Cimabue)、乔托(Giotto)、埃及和拜占庭艺术,庞贝(Pompeii)、法雍(Fayoum)和塞尚是他的指路灯。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做成一件能够“左右逢源”的作品,就像他经常说的——既能作为独立于主题之外自在的事物,又是给定主题的复制品。其表现形式,按贾科梅蒂的提法叫“相似性(likeness)或“复制(copy)”,却是某种无法企及之物,只有靠“失败”方能实现。与贝克特(Beckett)所说的“失败”不同,贾科梅蒂的“失败”最终达到的是“圆满结局(happyend)”——贝克特则称之为不可复原(échec à recupération)。贾科梅蒂常说:“埃及的胳膊最像一只胳膊”。而对他来说,与真实最不“相像”的画则是文艺复兴盛期的油画作品。无论贾科梅蒂如何景仰像雷纳(Le Nain)的《马车》(The Cart,1641年,巴黎卢浮宫)这一类作品,他内心其实很肯定:这一类作品确实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显而易见,在贾科梅蒂的理论核心中有一点矛盾,他自己可能也尚未意识到:一方面他认为抽象画是走进了死胡同,是找不到出路的;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莱南一类的具象派绘画也没有重振旗鼓的可能性。原因何在?这是不是正因为,在贾科梅蒂看来,“看”的乐趣与“画”的行为两者是完全脱节的,或者是让两者联合起来的艺术天才已经遗落,如今只属于某个已逝的黄金时代?抑或,去观看、感受某些东西,被它们所感动并把它们画下来,这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因为以现代主义标准来看这太过稚嫩?当然是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贾科梅蒂经常颇为自得地揶揄:尽管他的地位处于”peintres de dimanche”(业余艺术家)之列,他的作品却总能够与抽象派画家们同台展出。

由于叛离了超现实主义阵营,贾科梅蒂遭到了他们的敌意和蔑视——超现实主义者说他“沦落成了一个印象派”(在前者看来天下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此了)。贾科梅蒂发现自己被再度孤立了。但这一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某种程度上,超现实主义者们所获得的光环在其它领域也熠熠生辉,长盛不衰;而另一方面,贾科梅蒂与当时著名的室内装潢设计师让-密歇尔·弗兰克(Jean-Michel Frank)的协作(那是他被布勒东“逐出山门”的主要原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艺术与时尚的领域是互相交融又相互依存的,如能在其中一个领域获得成功,在另一个领域往往也能‘一荣俱荣’。阿尔贝托很快发现自己已进军巴黎时尚圈,他藉以作为入场券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大有前途的艺术家,更是让-密歇尔·弗兰克的合作者。巴黎的上流社会立即就接纳了阿尔贝托”。[9]
阿尔贝托和弟弟迭戈共同创作的作品(迭戈又自行对这些作品作了进一步的加工)立时风靡一时。他的雕塑作品也追随其后。世人——至少是其中最开明的一部分——从来都是眷顾他的。哪怕是在二战刚结束、三十年代的轻佻浅薄之风让位给战后初期的庄严肃穆的那段时期里也是如此。诸如《杆上的人头》(Head of a Man on a Rod,1947年)——与朱利奥·冈萨雷斯(Julio Gonzales,1876-1942年)那影响深远的《蒙特塞拉特岛之头颅》(Head of Montserrat,1941-1942年)并非没有渊源——的这类作品甫一问世就立即引起反响。然而,贾科梅蒂那些单薄脆弱的人像作品再一次被解读者们赋予了文学性的内容,而且这一次还染上了实存主义(存在主义)的寓意和萨特的祝福。萨特第一次见到贾科梅蒂是在1939年,1947年写了一篇论述贾科梅蒂的重要论文。[10]众多作家和诗人构筑了贾科梅蒂的生活天地,萨特是其中之一。这当中也有贾科梅蒂最亲密的朋友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极富人格魅力。他的机智风趣,他的如珠妙语,还有他对含混、繁复和优雅的爱好今天难以阐明,就是当时的人们也觉得无从捕捉。因而为他写传记的须是一位与他气质相近的作家,这就跟一首诗的译者不能与诗人本人的性情相去太远一个道理。为贾科梅蒂作传也就是按照写生、完全依样画葫芦地为他画像,按照生活原样来表达。然而,唉,毫无疑问这是做不到的啊。想象是飘拂在作者与主题之间的一层无形帷幕,它会导致自我投射(self-projection)、虚构杜撰,而这些正是小说而非传记赖以成形的母体。詹姆斯·洛德选择的是写一部传记体小说,而非采用传统的轻快笔法写一个人的所谓“生平”。这部小说动用了各式各样的原始资料(其中307种已经列成清单,但更多的资料尚未注明),包括回忆录、事实真相、杂谈、轶闻……大量素材彼此交织,描绘出一幅时代的宏大画卷。既然有意冒险一试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作家在某个细节缺失时就有理由依靠自己的想象来填补空白。尽管洛德与贾科梅蒂有着长期的交谊,但对于后者的生平他也不可能全部了如指掌。
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介绍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文章里写道:“我们所推崇的笛福不是一位能干的新闻记者,而是一位运用了能干的新闻记者笔法的小说家。笛福自己定会对人们加给他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这一头衔感到惊惶失措。他下笔目的在于,通过一种看似草率仓促、未经深思熟虑的即时叙事风格道出事实真相……”。[11]而洛德在他的第一本书《贾科梅蒂肖像》[12]中所运用的正是“能干的新闻记者”的笔法;当然,在他的第二本书、即那部传记巨作《贾科梅蒂传》中,洛德也竭力坚持发掘事实。这部传记受到了与贾科梅蒂素昧平生的评论家们的好评,但却在阿尔贝托的亲朋好友中激起了强烈不满,他们当中一些人还发表了一篇宣言,抗议他“对我们所熟知的人的歪曲描写”。我想可能许多人都会认同大卫·席尔维斯特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这本书在描写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事件时显得资料颇为详实,可一写到那些我十分清楚的事情时却顿顿失实”。[13]
倒是詹姆斯·洛德那部薄薄的《贾科梅蒂肖像》更为准确生动地表现了贾科梅蒂的机智、幽默感和智慧,果然名不虚传。贾科梅蒂曾为洛德画过十八次静坐肖像,在这本书里,洛德精确又点到为止地记录了他在这十八次静坐期间的所见所闻。这本仅六十八页的小书堪称新闻领域的一册玲珑杰作,但却非传记。这些年来,传记领域最坏的例子是那部以塞缪尔·贝克特的生平为对象的未经授权的传记。传主反对这项计划。它的作者只见过贝克特一面,他在写后者“生平”时是伤害外加嘲弄,已故的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辛姆·波切特生平”[14]。[15]在为一位艺术家作传时,作者如果偏向心理分析方面,就会妨碍艺术家作品的震撼力甚至误导读者。要知道,对真正的艺术家而言,生活中的种种细节琐事都只是灰烬,就好像贾科梅蒂,他为艺术焚烧了自己的生命。
*本文节选自《贾科梅蒂:不可为而为之》,《具象表现绘画文选》,许江、焦小健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原文写于1988年,载《纽约书评》,第36卷,第8号,1989年5月18日,第20-24页。发表时作了删节,原题为《贾科梅蒂的密码》(Giacometti's Code)。[1]参见瓦雷里·弗莱彻,1988年,第106页。——原注[2]贾科梅蒂致马蒂斯的信,1947年,同上引。——原注[5]詹姆斯·洛德,1983年,第154页。——原注[7]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佳年华》(The Prime of Life,1960年);参见上引洛德传记,第154页。——原注[8]詹姆斯·洛德,1983年,第155页。——原注[10]让-保尔·萨特“绝对者之追寻”(La recherche de I'absolu),载于《当代》(Les Temps Modernes),巴黎,1948年1月,第1153-1163页。——原注[11]丹尼尔·笛福:《灾年记》(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Harmondsworth,Middlesex,1966年。——原注[12]詹姆斯·洛德:《贾科梅蒂肖像〉(A Giacometti Portrait),现代艺术馆,纽约,1965年。——原注[13]大卫·席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贾科梅蒂和培根”(Giacometti and Bacon),《伦敦书评》,1987年3月19日,第8-9页。——原注[14]这是说理查德·埃尔曼讽刺传记作者严重失实,塞缪尔·贝克特(Sammuel Beckett)就变成了辛姆·波切特(Sim Botchit)。——校注[15]理查德·埃尔曼:“辛姆·波切特生平”(The Life of Sim Botchit),载《纽约书评》,1978年6月15日,第3-8页。——原注
光达美术馆 光达美术馆是以收藏、研究、展示为主的民营美术馆,座落于杭城南宋皇城遗址玉皇山南麓。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有着丰富的专业级藏品、多元的艺术空间,致力打造一个拥有论坛讲座、艺术沙龙、公共互动、学术研究及艺术衍生品推广等多项发展的艺术空间。
85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作者:光达美术馆
特别声明:本文为艺术头条自媒体平台“艺术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艺术头条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