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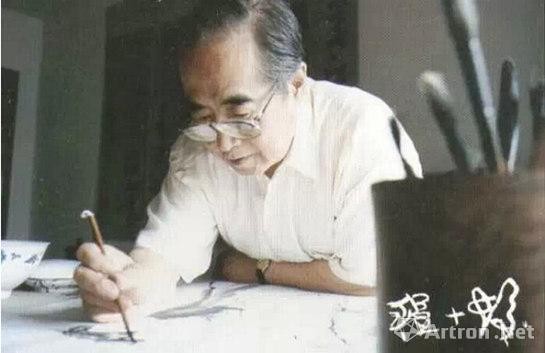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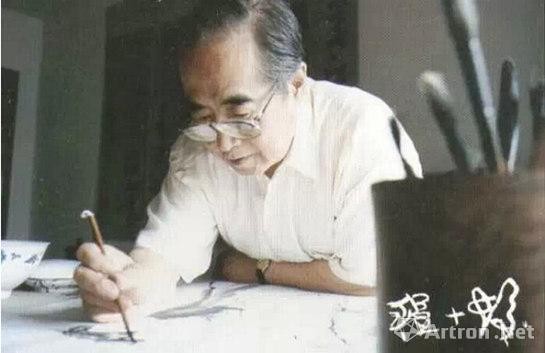
程十发
我拿程先生的画只当图本看,已有三十载,而当作读本细读之,则还是近年的事。
读画不同于看画或观画,看画观画养眼而已,读画却养心增智、大裨画艺,诚为一种上乘的功课。读画的自觉及其能力的获得并非易事,它是一个长而大的软性工程,须假以时日渐入佳境。最低限度,画是看的,通常的情形也正是如此。纵使能于看画中生些浅近的观想,仍未改生理性眼球消费的性质。本来一幅画以二维展示方式直呈受众,受众复以直观方式受之,其间并无大病。只是仅这样一来一往是断没有深度讯息交流的,于是乎个中殷殷厚味,便只好付诸乌有。倘若看画果如观花,有则有之、无则无之,令全无遮蔽和增殖,又凭什么把这浅薄的玩意儿标榜为大国文化。就算有人不肯追高,没拿它当文化,只充以牛眼观之,也不免因过于直白而于趣味上颇嫌寡淡……
那么,该如何在一幅画中看到更多?如何去深究画面背后藏匿着的心相和种种巧置?私意以为易“看”为“读”,即以破解的努力去读画,才是法门。而大凡读画,必有三问:一问谁画、二问画什么、三问怎么画。有此三问,则必有三读,唯其三读之后才能生正解。由于当下方便,我想在此请程先生之画入题,化其三问为三读,铺成其文。鉴于发老画虽众多,仍具足“类”的纯度,故不拟具体到某一帧某一幅,而是笼而统之地读。

程十发 《丽人行》

程十发 《镜心》

程十发 《竹花》
先是第一问,“谁画的”,答为松江十发居士所作,其为当代海派掌门,自号“云间十发”,可见已自许董其昌、赵左的“云间”一脉。此公九岁之幼即已习画,弱冠之龄便入名校,是个早慧的学人。如此庙也好、经也好、慧根也好,遂使他日后修行一路无碍,正旨得享。程先生的聪明素有口碑。聪明人画聪明画,本是水到渠成的便宜事,但程先生是个警醒之人,不愿被聪明所误,故其用笔求老,用墨求生,用形求拙,直把个天赋聪明沉潜在一纸生拙天真之中。“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此乃兵家谋略,屡使得之者胜出,似这等难参的诡道,程老却能在画中悟得,足见其变通之力。
另则,程老国学深厚学脉有绪,又是个长于广取博采的通达人,但看他放笔纸上,却又是个偏执的正统异己,自有立法,一派不屑于人同逆世而独立之概,此中也不乏玄机吧。观程先生画,既非“老古董”,又非“学院式”,更不是民艺调或西洋腔,只好呼之曰“程氏图式”了。“守”与“变”,向来是一对矛盾范畴,叹天下画者多陷于一方。程先生既于二者都有卓卓事功,将其视之为雅驯的风格主义者当无大错。这是值得推广的人格配置,只须调试得当,就能像永动机那样近于“永动”,令生机长存。当然,事情并非如此机械,其另有玄机,诚如发老说的:“中国画在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继承传统和对生活一往情深的基础上的”。我们反观程先生,先生对诸多雅事总是兴味不减,甚而不减反增,是个童心不老的玩人;先生书画传家,收藏成癖,是为痴心,其不仅痴物,而且痴人。有先生印一方为证,印文曰:“十发梦见悔公”。其心追陈公老莲若此。又先生作画选材甚富,有目共睹,因其所爱甚富也,乃至画一种爱一种,爱一种画一种,样样未肯相弃,是为爱心。由此可见,程先生说的“一往情深”,实乃用真心炼成的心语。古曰笔法就是心法,就是人法。程先生人既如此,画亦当如此。这是“人画合一”的大性情大境界。
至于怎样才能达此境界,程老自有妙悟,他说首先,“人家一看作品必须认得是谁画的”;其次,“画家所表达的内容,一定是要自己所喜欢的”。凭这两句话,谁画的问题已回答了,即答案在画中;画什么的问题也回答了,即要兴趣导向。兴趣导向之于绘画本位是肯定不假的,固然画家须有社会和道德担当,也未必于其间“兴趣”不起来,只要画家够厚道,便不是问题。
再说程老的选材,即他画什么的问题。他博爱于天地间,选材的路向自当是多样的。其间有崇高的悲情的,如历史人物系列;有幸福感的喜乐的,如人畜相呼的蜜意小品;还有一类在我看来是奇诡的意相探险,如他追梦般的山水造境。这些题材应该都是发老所喜欢的,喜欢其文史内涵的有之;喜欢其物态玲珑个性可爱的有之;喜欢人尽喜欢的亦有之。不妨猜想,程老作为一代风格派大家,其最为心仪的会是那些能为他腾出足够个性空间的可作为形式借口的内容,这情形与唯美主义者旨趣相仿。无须讳言,其实,任何天才画家的真正乐趣和感动即在于此,即在于管他什么内容,只要能为其插上如意的形式之翼,任其放飞在审美的天空——这样一份窃喜之中。
美术学院中曾习用一个有力的短语:“不在画什么,只在怎么画”。犹言形式表现之首要。从程先生的大量画作看,他是首肯这一主张的。面对他的画,你可以说它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很好,但你不应该借此断定其形式是由内容导出,因为内容先行或形式先行,都是画案上的常事。更何况形式立意本身便是可以充作内容去肇始一个画面的。如果说一幅画乃始于一个冲动,那么,这样的冲动既可以来自红色的花朵,也可以来自花朵的红色……即便在作画过程中,二者的主宾关系也常是随机颠倒的,程先生在此间定然早已炼成了百变的翻云覆雨手。有一个共识,内容的一半是形式,形式的一半是内容。它们本是和谐一体的,互为表里,而且应事而变。曾有人偏废形式突出主题,结果形式死了,内容也空了;也曾有人将形式进行到底,到头来内容死了,形式也空了。其实到此,“第三问”已解了一半。
那么,在剔去了与内容的纠葛之后,所剩的形式又是些什么呢?我想是纯符号纯图式纯技法外加纯粹音乐感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无从触摸,但就眼睛而言,却很真实,很有能量,因其是理性与人性的合力,当然内中还有直觉、错觉和偏执。我们可以在程先生的画中感知它们的存在。由于程老是个神经强健的形式实现者,倾向于强化各种元素,这颇使我们的解读变得明白畅晓。比如在他坚实而强烈的线结构中,我们读到了坦露的理性——那种为他个案的《病态结构》作支撑的理性;同样的,在他那剑走偏锋的悬浮笔态中,我们读到了人性,一种极易被撩拨起激情的可错的人性;我们甚至读到了二者的合力,即人的盲动力与理性静力的合力,以及由种种机巧做成的间于其内的缓冲部件。自然,这不是他的全部,因为至少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即程先生在“拿来”和“变通”的时候所显示的极为强大的消化力。他那年轻的个人图式如同功率强劲的粉碎机,把李流芳的湿笔法消化了,把陈老莲的白描法消化了,把徐渭的疯狂意态消化了,把霍去病墓石兽群的浑然无形消化了,把江南民间泥人稚拙可爱的变形消化了,而且,消化到了分子水平。
经由上述三读,可知程先生是独特的,其画艺更是独特。王伯敏先生评述得好:“程十发,就是程十发”。他用温馨庸常的胸怀面对视域世界,却以文化公理和极个人的方式去组装和再造它们。他因此输掉了大众化正统化的那份人人得享的温适,却为自己赢回了弥足珍贵的“个人面孔”。尽管他的画作多不是尽善尽美的那种,而且“背离”又是那样地出格,但其认识论价值远胜过那些不敢逾矩却看似完美的画面。他的确深刻地启示了我们。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脱稿于司雨堂
作者:尉晓榕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