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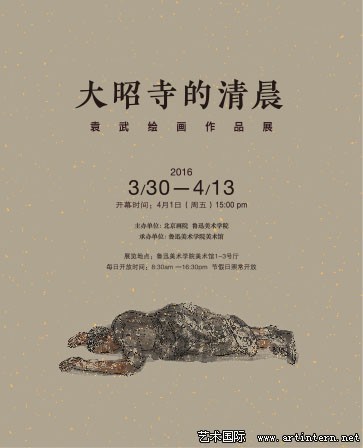
2016-03-25 1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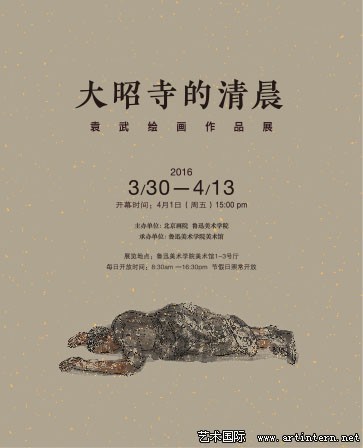
一
真正优秀的作品,出自心灵的作品,过多地对主题思想的解说与精神价值指向的评论,是多余的。袁武先生的《大昭寺的早晨》是感性学之物,画面形式语言即精神、思想、主题的标出,放眼一望,旋可震撼心灵,目击即道存,本不需过多解说。
我在中国美术馆看袁武先生的《大昭寺的早晨》时的一系列感受,后来,在读到袁武自撰的《西藏行日记》一文时,发现:其实,他自己早就都写到了,这是在艺术的技术表达上,形式语言运用精准、适恰使然。当袁武走进藏人的宗教空间,看到了形象、年龄、眼神、身份有异,但心境相同、虔诚无异之时,他因此而震撼,有了创作的冲动,那冲动,使他不期然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是袁武先生在《西藏行日记》中的自述,却也正是我在中国美术馆看到袁武《大昭寺的早晨》时,不期而至的真实感受。
经过接连两日盘桓在大昭寺清晨的烟雾之中,身入其境、在忘我地近距离观察,切身其中、有了自我体验之后,袁武感受到了眼前人群的壮美、圣洁,知道了自己“要表达的是宗教的力量与信仰的崇高。”(见许宏泉主编《边缘》第31辑、第30页,袁武自撰《西藏行日记》所载片段)2014年3月2日,《关切的向度》六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人们看到袁武《大昭寺的早晨》时,应该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他所表达的“宗教的力量与信仰的崇高”:座南面北的墙面上,30个 朝拜的人的侧面头像,形象、年龄、眼神、身份有异,但均朝向一个方向,状如砖砌,被统一于一片晨辉之中。这是30个可以独立成篇的朝拜的人的侧面头像,每一个人分解出来,都可以是一件独立的作品;但现在这是一件作品,不可分割——晨辉具有肖像性,是希望、是蓬勃,也是祝福的象征,不过,袁武绝对没有“放大”这一肖像性,没有“装饰”这种肖像性,而也正因此,在极精心而似不经意中,朴素产生了真实,真实生成了朴素,画面缘此而特别震撼人心。
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不是猎奇,不是采风,他忠实于看到对象时的心灵感动,忠实于表现因心灵颤动而产生的精神回响,进而,忠实于他看到的对象时自我生命升华时的那种高峰体验。所以,这件作品,实质上,也就最终成为欣赏者的朝拜对象。这就表明,由于这是:心灵颤动→引发回响→生命升华的产物,所以,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不是一般的表现自己看到“外自然”时的植入式的审美感受的再现或曰显现,袁武先生的创作的过程,在本质上,乃是自我心灵的振动与升华的还原式的生命体验之他的“内宇宙”中的再度被升华与被锤锻的那种更高层次的感悟和体验的“倾诉”过程。
所以,欣赏者面对袁武先生的《大昭寺的早晨》的那“一刹那”,其心灵、其生命,自然也会在“朝拜中”升华。面对袁武的这件作品,面对着这由慈祥和霭、恺切平易、沉毅恢弘的外在自然景观转换、升华成的视觉图像,我们的体验的是,一言难尽之眼前景观,已然被袁先生武先生的图像一语道尽——生命之所以如此壮美,正是因为有圣洁的信仰和对寻找生命归属持有的虔诚心态。
二
如前所述,袁武画《大昭寺的早晨》中的那些朝拜的人,其本身也是一次心灵的朝拜,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但由于那些朝拜的人是他的朝拜对象,所以,其作品标出的主题才最终不再是他的朝拜对象(那些顶礼礼拜、匍匐长拜的人),而是因“不拘外物”的虔诚的信仰而致使的心灵的神圣与洁净。于是,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这一作品,也就因此相应具有了成为欣赏者朝拜对象的潜在特质。
面对袁武先生的此件作品,通过阅读前述的他的自撰文,我们可以展开想象:画家在大昭寺状如潮涌的人流之中徜徉,本不想猎奇,突然,如同庄子不知周蝶,突然内心一震、有所感悟,于是,一个既有意义、又有意味的画面形式也就显现出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内心一震,有了这样的图像显现,“外自然”也就转自然而然换成了某种“内自然”中的秩序,而这是这秩序反转过来激活、升华了袁武先生的内心一震,使他的画面图像有了灵魂。
这就是说,通过身入其境、切身其中的体验,通过聚焦式的深度观察,袁武也许真的发现了伟大的“因明哲学”是雪域高原虔诚信仰的坚实的基石;于是,与这基石相联系的那些人才在他的知识结构中被重组、被再造。重要的事,也许,正是这支撑于藏人内心深处而外显于他们的言行举止的“因明哲学”的“宗”、“因”、“喻”之逻辑方式,潜在地成就了袁武的这一视觉感受→形上化了的精神丰碑。因为,通过《大昭寺的早晨》里的那些朝拜的人,袁武以“符号学”意义上的“相似性”而“标出”的终极主题,实质指向的是洁净的心灵、虔诚的信仰、崇高的生命,乃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类必然共仰的不可撼动的精神丰碑。
具体而言:在中国美术馆二楼的某个整整一面的座南面北的墙面上,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置阵虽状如砖砌,但若不是袁武那“被圣洁意志感动了的灵魂做了自我精神生命的导师”,难以想象他何以会如此置阵布局。于是,而这样置阵布局的结果,也就使得“被圣洁意志感动了的灵魂做了自我精神生命的导师”的价值指向是双关的:画家被生活感动,精神生命得以升华,而我们被画家的作品感动,精神生命同样得以升华。有论者认为:在当代,“盲目的社会发展会给人类带来道德的迟钝,限制了人们的智能活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人的心理不平衡,导致了生命意义的泯失与陨灭,这与人类的“核心文化时代”共同追求的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不啻天壤之别。”在我们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武的《大昭寺的早上》,指向的是“人”的“心灵纯真”的回归,标示的是画面给出的不可“解构”的“人”的质朴而纯净的“生命自意识”的回归。这就是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的终极价值,是人类社会不应该丢弃的宝贵的精神指归。
当然,绘画作为感性学之物,依据的主要是技术语言表达而不可能是观念的直白切入。20世纪发展、壮大起来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在袁武这一代画家手中,借助“语言学转向”语境之中“无所不在”地弥漫着的“智性因素”,而有了崭新的高度。一个画家的技术语言与他的心路历程是息息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在“经验主义哲学”成为青年画家创作思想主臬的时代,正在央美攻读研究生的袁武的技术语言,一方面,重又受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晚期在中国诸美术学院诸多前辈学者共同建构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系统的全覆盖浇灌,另一方面,在这里,袁武不仅得天独厚,能集20世纪发展、壮大起来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之大成,而且时代思潮(’85美术思潮)的变迁,也教会了袁武如何在解构了的多元文化中建构(结构)自己的个性化语言手法。现实主义写实手法,对袁武而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艺术生命的起点,而当时波诡云涌的时代思潮滋养出的崭新的艺术理念与手法,对袁武而言,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方向标;二者,异中有同,共同构成了袁武此后“道技合一”的艺术发展的基石。他的《大昭寺的早晨》的图像新变,其“技术哲学”基础,盖来源于斯,这使他的不违“外世界”的艺术上的“内世界”的“图像再造”成为可能。(详情可参袁武自撰《甘南行——记和姚有多先生写生的日子》及《怀念卢沉先生》等文章,文见郭艳著《袁武》第176—178页、第179—18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
袁武先生的《大昭寺的早晨》,那“状如砖砌”的形式美感构成,无疑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极大的满足与情感上的特殊的享受,表明他已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水墨”必须再次经受“现代性”的洗礼。2014年3月2日,《关切的向度》六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之时,袁武先生的《水不深》与他的《大昭寺的早晨》并列展出,这幅尺幅同样不小的画作置于《大昭寺的早晨》之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表达的主题直指社会现实,但内蕴“春秋笔法”,其凸显的象外意是中国儒家的“刚与烈”和“真与善”。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大昭寺的早晨》之左,是袁武先生的《耕耘在八大山人的土地》;从图像学研究出发,就会发现,这样的安排意味深长。《耕耘在八大山人的土地》,保证了袁武画雪域不再是猎奇,同样是“春秋笔法”中的仁学的从容、中和但不失日新适时而变的意志,与道家思想的空灵、尚朴及其天地与人合一的精神,不仅助力了袁武表达雪域的圣洁,而且,也使袁武的雪域表达最终能成为人们精神的灯塔。这多少说明,袁武已经把他所画的朝拜者放到当代的文化语境进行技术转换,以此提醒欣赏者直面那些朝拜者的真实的生命状态,并以此发现他们的“内世界”的“光辉”——事实上,从画面中我们看到,这“光辉”,本质上是由执著、真诚与崇敬点燃的,所以,经过前述的那样的“状如砖砌”的重组,绘画欣赏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看”之于“目”的过程,实际上也即是一个“烙”印于“心”的过程。于是,欣赏者在画面“洞见到”的敞开的意义空间,便与画家心心相印、与画面泯然无间,袁武先生正是因此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艺术领域的地位的。
分析、研究袁武先生的《大昭寺的早晨》的图像学意义,无疑应该同时考虑在那个早晨被感动的这个被称为袁武的人的“吾心”的实质器量。因为,正是这“器量”使得他的《大昭寺的早晨》的图像,标出了有声语言、文字语言难以表达的人的内在精神之实有状态;显现了人的形而上的抽象意识的深度诉求,让人通过其图像不是思考而是认同他的文化归属和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在创作《大昭寺的早晨》之前,袁武通过《霸王别姬》、通过《抗联》、通过《水不深》、通过《在八大山人的土地耕耘》的心理积淀,已让自己精神生命的张力能在图像中自由凸显;简言之,通过《大昭寺的早晨》,袁武已将近现代百余年先进的中国人的文化追求,通过时代的文化思考而在现实层面推出;让他的绘画图像,已能引领我们精神的回归;这就是:在信仰的清晨的光芒中,社会学意义上的“游牧的个体生命”不再被诱惑,精神因此聚拢成有所皈依的形而上族群,日常经验上升到形而上的文化境界;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正是通过如是的“技术哲学”而显现出了“语言学转向”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图像力量的。
三
如同书法由单体字组织成篇,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置阵上有“计白当黑”的图像意识。重要的是,只有被生活真正感动,才能发现其统一之中的差异的美;而只有心灵体验上升到形而上的文化境界,才能有效表达出绘画上的接受美学意义上的境外象,意外味。
中国书法的深处,不在单体字的美,而是书法的整体感觉上的气息、意象、格调、品味和境界合成中一起创造了一个文化的世界。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社会各阶层的人,不同身份年龄的人,在某个早晨被统一于共同的生命呼吸、共同的心灵节奏之中;其置阵布势的灵感,不能不说与他青年时有着忘年之交的书法老师金意庵、周昔非两人的影响息息相关。概言之,他对他青年时有着忘年之交的两位书法老师一直到现在都持有“敬畏之心”,而正是这“敬畏之心”,潜在地、不期然地成就了他的《大昭寺的早晨》的置阵的布势或曰章法的格局(详请请参袁武自撰文《怀念老师周昔非先生》及《我与金意庵先生》,文见郭艳著《袁武》第193—195页、第200—20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
当然,书法的影响不仅仅在置阵布势,请看:有人在双手合十的瞬间静止时,曾甩的手钏似乎还在锵锵作响,静中有动,而正处于缓慢双手合十的运动状态的老太太,神态上却是静止的。这之中,袁武不炫技,画得极为从容,但有神来之笔,所以我们能看得愉快,心观得敞亮,意会得洞达。此外,再请看《大昭寺的早晨》的笔墨技法:勾、垛、扫、渍、勒,批麻、乱柴、云卷、荆编、吹絮,意象化的趣味性之中,终成书写性前提下的“装饰→意象”效果。而正是这书写性前提下的“装饰→意象”效果,有效地支持了袁武在设色上拉开了与现实美的距离,具体而言,在《大昭寺的早晨》的设色上,构思之高迈,如地图之设色;尽量不超过四色;钴蓝色相如天,藏红如焰,石绿则青春,古铜色当有崇高感,金、白、黑,固凸显出纯净与力量,标出的是抽象与具象无间,形成了简洁的力量。这之中,袁武同样不炫技,他追求的是技术语言之中的普世价值,所以,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的真诚的魅力。
长期以来,袁武一以贯之地或直面现实生活进行具有当代性意义的前沿样式探索;或于历史文本之中挖掘前人的文化能量进行如何使之升格的研究;二者的结合,使得他的《大昭寺的早晨》,能在《老子》所说的“玄同”层面,既有抽象又有形象,二者的巧妙结合,使得他的作品既有形上意味、又有形下显现,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情感主义的。五代梁时的荆浩的《笔法记》曾提出用笔有四势:筋、肉、骨、气,在中国文化语境,生命之命,即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也是无法直接面对的一种隐形的存在,而正是“命”的这样规定性,使得中国画的意象通过笔墨这个中介“传神”而人格化,这是中国的水墨画家无不重视书法的基本原因,在如是的意义上,《大昭寺的早晨》给我们的启迪是,对绘画而言,类似书法这样的精神与技法的渗透、挪用,自然重要,但关键还是作品本身要站得住。不可炫技,要有世界眼光襟怀和思想深度,民族的并不一定要强荐于世界,人文关怀才是我们终究的普世价值。
如何画,要有道理,对这个道理的判断,是功力使然。重整山河式的如砌墙般的置陈布势,是袁武忠实于客体、忠实于情感、忠实于人文文化、忠实于心灵的独到的真诚使然。正是这种真诚,使得袁武先生的绘画形象,成为自在的生命体,能够呼吸,有灵魂、有血液,能让欣赏者的呼吸,随画中人一起呼吸、一起脉动,一起参与修行。以及,让我们对生命的认同一点点地生发,让我们的忘我的灵魂,通过画面笔墨在画面行走、奔跑、跳跃、翱翔。通过有意味的用笔、有意味的设色,普通的中国画的材质变得令人耳目一新,使袁武先生最终能够创造出与信仰的价值与意义有关的图腾。此时,我们好像不是在“观看” ,而是在“体验”,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尊严和人性高贵的期盼。
四
立足于绘画创作是一种需要,一种内心的需要,一种生命的需要,袁武先生在创作中,对于他所使用的工具材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袁武曾说:“中国画的笔墨纸砚,在不同的画家手中会有部署的属性和特征。” 这说明,材料是重要的,但与材料血脉相系、逻辑相联的形式语言表达,及其画家本人的修养,是更为重要的。
在创作中,袁武尊重客体,但迁想发挥,他会认真研究所欲表现的对象的空间、组织、结构、光色、颜彩,但最终,他会“心起丘壑”、“重整河山”。重要的是,对于空间的探索,袁武不止于物理空间的表现,同时,他还极为注重表达更深层的,形而上的文化空间的意义。这就使得他的作品,一方面,在与当今社会文化所需的价值指向紧密相连的同时,而让自己的艺术语言根植于中国文化对人文涵养的深度观照之中;另一方面,则是据此通过将现实主义话语系统与抽象表现主义话语语用在自己原创性技法语言的建构语境融会贯通,由此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充满独特魅力的手法语言,并以此不仅使他“以文载道”,而且,能让你“目击道存”。在这个意义上,欣赏袁武的作品,必定会是一个很敞亮的过程。
袁武曾带队前往西藏写生,他曾说,此前,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画家从未去过西藏,大多是通过图片、音像、文字了解藏区,“深入生活”与“写生再现”并不是一个概念,写生再现是为完成画面,而深入生活则是生命进入即下生活链接的文化河流,前者是表现,后者是感受。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武的作品一般都不是张力强烈的实验性的,也不是样式特别出彩的现代性的(譬如拼贴式的)。他甚至有一些保守。这是一种在“水墨前卫阵营”中的“保守”。简言之,袁武是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所说的现代性的“颓废性”的另一极切入他的人文关怀的;信奉本雅明的观点的画家,注重的往往是人之现代社会中的惶恐不安,袁武画的是信仰与生命安吉的关系的给出。比较之下,便可看出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是中国的儒家式的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在作品中,清晨的大昭寺前,熙熙攘攘如潮交激的整体意象,被分解聚焦,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他的“敬心”与“爱心”,而达到深刻的、细致的刻画,表达出对生命的尊重。而也正是这样的“敬心”与“爱心”,使得诸如“素描”这样的功底,诸如“书法”这样的修养,以及,诸如“审美判断”这样的功力,也就自然成为一种内在能力与绘画的笔墨媒介、与绘画的工具媒介密切相联。
2014年3月2日,《关切的向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参展的六个人,都是用水墨寻找现代中国人的人的灵魂的难得的翘楚型艺术家。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中的朝拜的人物图像,正是艺术家与承载人的灵魂的水墨材质对话的产物。这件作品,也让我们的灵魂不由自主被振动、被升华,于是,我们相信,清晨,当朝拜的人如多股水流在大昭寺前汇聚成一条统一的朝拜的人流,展现在画家面前时,一定会振动画家的心灵,此时是他的真诚使他不是去猎奇,而是体验到了人间崇高而纯粹的美和善,是心灵被朝拜人的虔诚无私、质朴无欲的情感和态度振动,他看到的是雪域高原古老的、原生态的人的生存方式和对待对生命的态度的终极体现,这涤冲着他的心灵,由此画家会觉解到一个人应有的对待生命态度与对待生命的意义,非此,就不会有《大昭寺的早晨》对我们的振动。
中国人的“先立乎其大”,就是原则在先。在中国人的艺文思想中,理念“意”是具体的物象没法直接表达的,但正是它能打开欣赏者的心门,而也正基于此,中国人的“先立乎其大”,绝不是民粹主义的;当代著名德国戏剧导演托马斯·欧斯特迈耶曾说过:“灵魂在身体之外观万象,做了自己一生的导师”,我们相信,《大昭寺的早晨》,是袁武的灵魂在身体之外与眼前之象交流、碰撞、对话、聆听、觉悟,做了一次自己的心灵的导师。他的灵魂由此升华,我们的灵魂也因此被振动。《大昭寺的早晨》的语言由此变得鲜活,绘画创作成为灵肉一体的精湛演绎,这是他在当下时代为我们所画,不可模仿,也无需复制。
以前,袁武曾画有《阿拉山口的雪》,是戏剧性、情节化的。《大昭寺的早晨》的形式,没有戏剧性情节,也没有过强的情节性表现。如果过于戏剧化、情节化,就会稀释掉水墨本体意味对我们的震动。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的高迈处,就在这形式不是戏剧的、也不是文学的,并且,还主要不是视觉的,而是直指心灵的水墨本体的。其实,袁武的《大昭寺的早晨》,本质上并没有宗教背景、也没有政治意味,他摈弃了精神政治学雾霾,在语言学转向意义上,他逆转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的“宏大叙事”,本质上,这应是后现代语境中的宏大叙事的另种别裁,袁武先生表达的是人类永恒但微小的普遍的精神感情,以及,这种普遍的精神感情在被剥离出来的个体身上的微小变化。因其微小之微小,袁武的作品没有如本雅明的一些追随者的作品那样有暂时令人读不懂的焦虑,所以它却会让我们在看到它的那一瞬始,即能成为精神财富和精神动能自此而陪伴、照亮我们的精神生命一路前行。
2014年4月15日于北京东华门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付京生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