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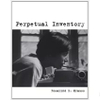
2018-01-10 17:37

摘要: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艺术批评家,罗萨琳·克劳斯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出发,结合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等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进行哲学艺术批评。文章在综述克劳斯哲学艺术批评的同时,对她独特的哲学式的格子和非形理论进行探究,从而展现了现代主义神话背后的逻辑所在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精髓。由此,克劳斯通过哲学式的艺术批评,在揭开现代主义面纱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形式主义向后形式主义的转变。
格子理论—现代主义神话
格子的出现是一种现代主义现象,是艺术史向现代艺术的转变的一个媒介和再现。与此同时,格子反对文学、叙述和话语,她把自己囿于一个专门的视觉性世界,实际上,从这几点看出,格子理论仍旧摆脱不了格林伯格那种普遍性且跨越历史的形式。
格子是克劳斯哲学艺术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基于克劳斯的艺术批评的哲学化,同时由于格子在克劳斯著作中采用了分析哲学语言的风格,使得格子在视觉艺术的运用上显示出自身的形而上精神和形式上的本质呈现,这就使得格子在克劳斯艺术批评中成为一个既定的美学概念。
格子在演绎成为一个美学概念的过程中,克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首先从格子的时间和空间特性着手。从空间方面来说,格子表达了艺术空间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格子图像是一种来自于自身的美学规范。格子的有序性既显示了图像空间的纯粹关系,又表明了这种结构与自然物体处于相分离和相关联的境地。由此,从空间上,格子的美学概念在于她自身的纯粹性和与再现物之间的关系性。也就是,在视觉艺术空间上,抽离掉所有的由视觉幻化成的空间,剩下的只有一种结构:格子。这里,格子既是空间的纯粹结构,又是空间的本质存在。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格子即作为本体被研究,又把自身的形式与内容合二为一,从而在克劳斯的格子概念中,我们看到了格子在形式主义中所具有的中心和本质。

Rosalind Krauss - Perpetual Inventory (October Books), book cover
从时间上分析,克劳斯把二十世纪格子现象作为是视觉艺术的现代性特征显现。在这里,克劳斯强调了现代艺术与过去和传统的决裂,也正是这一点成为克劳斯走到格林伯格的对立面。回溯格子历史,早期的格子与透视学有关,但并不算最早的例子。如果说透视呈现了画像与真实参照物之间的关系,那么格子无关于这种关系,因为如上所述,格子具有自身的纯粹性与关系性。通过格子的横线与纵线,物理平面与美学平面在格子上成为同一平面。然而这种唯物主义特质并非艺术家所要探寻的。对蒙德里安和马勒维奇来说,他们要探讨的是存在、思想和精神。他们认为“格子是通向“普遍”的楼梯,”在这点上,格子成为现代艺术家探寻思想的一种媒介。正如莱茵哈特的九方格子成为一种象征的符号。这样,格子在时间上成为通向现代主义的一个媒介,甚至成为现代主义的一个再现,因其本身就代表了某种精神和存在。
在诉诸格子作为象征符号的精神性征象标记过程中,克劳斯回溯了格子的精神发展历史,在这整个过程中,她运用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让格子从逻辑上和经验上成为自身的精神符号。克劳斯认为人们对格子的引进与十九世界科学掌管精神物质相分裂有关。另外,在十九世纪,当艺术成为宗教情感避难所的时候,她也成了信仰的世俗形式,那么艺术与精神的对等与互为就成为人们表达世俗与神圣的支撑点。而对格子来说,她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即它在现代艺术的特殊空间中所达的冗长生命,应该归因于它能掌控羞于在同一层面涉及艺术与精神的这种所谓的耻辱,它能同时掩藏和揭露这种耻辱”(Krauss 12)。由此,她担负起扮演象征和神话的角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十九世纪人们对生理光学文学的阐释通常诉诸于格子,那么,克劳斯说,“对于那些要从科学角度来加强理解视觉的艺术家来说,格子就是一个知识迷宫”(15)。而格子自身的抽象性特征同时传达了其中的一个现象,即知觉屏与真实世界的分离。由此,格子成为新印象主义的重要特征,也促使了修拉(Seurat)、希涅克(Signac)、克朗斯(Cross)和卢瑟(Luce)着迷于这种生理光学,以至于走向其对立面—象征主义。
这里,通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方法,从格子的纵向行列中导出了格子与象征主义之间的直接关系。如果要分析象征主义中的格子元素,那就是窗户,而窗户本身的透明与不透明使得画像呈现了某种现代主义特征。在这点上,克劳斯本着哲学思辨的精神,同时运用文学性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来分析窗玻璃,即窗玻璃是镜子又是某种东西,是流动和凝固,流动指向出生流 — 羊膜流,“源头”— “但接着流往静止的凝固或死亡中去 — 镜子的枯竭静止”(17)。由此,窗户成为一种符号,而这背后最本质的结构 — 格子,因为自身的抽象性,在象征主义范畴中,具有了自身的征象符号,正如窗栅是格子的表象呈现,具有着象征意义。因此克劳斯说,“在每一个二十世纪的格子背后都有一扇类似受压创伤的象征主义窗户”(17),比如在马蒂斯的窗户中,我们看到了格子的神话存在。

The violinist at the window,by Henri Matisse
从格子自身来分析,克劳斯认为格子具有精神分裂症特质。她具有离心和向心的悖论特质。离心显示了视觉艺术超越边框的现代能力,向心特质是格子与再现的关系呈现。
我们能从蒙德里安作品中向心与离心的格子特质看到,格子成为艺术家表达现实抽象性的媒介,也就是,在艺术家思考现实世界过程中,格子成为艺术家再现精神性的一种媒介。由于格子具有的最基本的抽象性,使得艺术家把格子的结构衍生到具有相同结构的元素上,比如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的数字和字母,对建筑空间的部分思考,人造符号系统的无限扩张,对三维格子、格状物的模式构建,风格派的作品,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的模块和格状物等诸如此类的运用,这里有显示超边框对表面去物质化的无限延伸的离心状态,从而展示了格子在空间中显示精神性的物质呈现。
另一方面,格子的向心状态比如阿尔弗莱德· 延森(Alfred Jensen)和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的作品中,其边框内格子被认为具有唯物性,正是这种格子的精神分裂症给艺术家们比如蒙德里安、亚伯斯(Albers)、凯利(Kelley)、勒维特提供了双向思考。

Twelve Events in a Dual Universe,by Alfred Jensen
既然格子在二十世纪艺术方面呈现出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特质,那么克劳斯认为应该从病因学而不是从历史或者发展方面来思考格子现象。这里的病因学指的是对格子进行类似化学实验背景那样去探究,也就是对产生格子现象背后的各个因子的探讨,去研究这些因子如何促成格子产生,并且以不同版本产生。这里,克劳斯用结构主义把格子放到艺术历史世界去考察。并且把格子美学放到音乐、舞蹈、雕塑等媒介中去考察。最终,克劳斯得出结论:“我们就会发现格子最现代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具备为反发展、反叙事、反历史充当典范或模型的能力”(22)。因为从格子本体论出发,格子对语言隔绝的特性使得格子具有了反指涉特征和反叙述特征。而格子结构中所具有的无时间性和无叙事性阻止了语言投射在视觉领域,这给格子带来了寂静感。在这点上,克劳斯用文学性语言进一步阐释格子的寂静美学,从万籁俱寂中听到了艺术的起源之声(参见《前卫艺术的原创性和其他现代主义神话》:“格子的寂静感不仅仅源自高效、彻底地反语言,也源自网眼阻止了外界物质的侵入,就像空旷的房间中没有脚步的回声,鸟儿飞过天空没有声响,海洋中没有急流一样。这是因为格子打破了自然的空间感,后者建立在纯粹的文化对象的有界表面之上。格子对自然和语言放逐的结果就是更多的沉默,它让很多艺术家听到了艺术的起源之声”(Krass 158))。 这里,我们领会到格子的形而上精神,是原初的那个无中心的中心,是无本源的本源,是关于原生态的概念。也正是基于此,格子让艺术家领会到某种关于艺术的原创性物质,而且这种图表纸的启示性结构保持了她的永远崭新和独特,这对于寻找源头的艺术家来说,无疑通过格子探寻艺术的源头似乎来得更加接近艺术的本质,而这源头显然成就了格子的神话角色。
格子的原生状态让格子成为自由的象征,但一成不变的格子又充满矛盾,对艺术家来说,当艺术家着迷于格子之时,却发现一方面困在其中,一方面又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自由。而当他们借助格子创作时,作品只有出现不断的重复,比如蒙德里安、阿尔伯斯、莱因哈特、阿格涅斯·马丁,这里,原创性与重复性这对相互对立的术语在格子中暴露了现代主义神话的本质性,而这对互相矛盾的术语本身呈现了现代主义的悖论所在,在现代主义那里,这对术语虽然不能合二为一,且是两个极端,但却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捆绑。但无论怎样,一旦艺术家试图诉诸格子进行艺术创作,即使把自身的特质内化进艺术品中,在克劳斯看来,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永远成不了格子的原创者,只有扮演重复者。
格子本应向我们敞开源头的秘密,也就是这源头处在不断重复或复制中,无论是逻辑上,结构上,还是语义上,它只能重复。然而,在艺术历史上,我们看到无数的艺术家把自己放置在这种困境中,不断重复这种逻辑上具有欺骗性的所谓的源头。格子的重复性本不应该存在错觉,但事实相反,图像表面的原生状态确实具有错觉性。对源头来说,画布表面与格子并非合二为一,如从最基本的结构来说,格子在画布上的呈现就是画布表面的再现。而且,这种再现就是一幅图形,也是抽离掉所有修辞视觉之后剩下的原生物体。具体来说,通过格子的网眼,它呈现了画布基本结构的形象,通过坐标网状系统,格子自身就成为了几何场域的隐喻,通过重复,格子展现了横向连续的无穷延伸,这样,格子并没有暴露图像表面,反而通过重复掩盖了后者。这里,如上所述,克劳斯再次提醒我们格子的精神分裂特征。
克劳斯进一步具体分析,艺术家的格子创作必定跟从某种所既定的画作,但格子的再现文本先于图像表面,并且试图阻止原初的图像表面成为源头,这是在图像表面之前都是些即要整合成图像场域的图像文本,这些图像文本从格子美学来说,也就是物理的、知觉的、关系的转变,比如从从绘画到壁画的重叠格子层,三维到二维的透视晶格,矩阵模型,以画框为参照的规则四边形状等。而这些从格子美学角度所呈现出来的再现文本正是蒙德里安他们所孜孜以求的图像源头,但是,基于格子的美学特征,从艺术家们试图揭开格子秘密之际,格子就在这种不断重复或复制中被撕裂着,从而产生了量产的概念。

Rosalind Krauss - The Optical Unconscious, book cover
艺术批评把图像表面的原生状态当作不透明性来处理,这是因为不透明性意味着非虚构性,也意味着类似单一性、唯一性、真实性、原创性、独创性诸如此类术语的形成,这些术语是现代主义的核心所在,但在克劳斯看来,这种不透明性就是一种虚构性。她因此通过语言学剖析从而暴露了里边的悖论所在。比如假定现代主义的愉悦层是自动指涉,那么,它必须产生于图像符号的非再现性和非透明性,基于这点,所指对一个具体能指来说就成多余了。但众所周知,能指是不能被具体化的,同时能指的客体对象和其属性只能属于想象范畴,而且,每一个能指是作为符号媒介对既定物的所指。由此,在符号链中,只存在这样的透明性,即坠入无边深渊的复制系统,并不存在不透明性。
在这点上,意指图像的格子通过再现,把超越于它自身的更早的格子系统的能指安置好,这就是现代主义的格子所要做的。比如罗丹的铸型就体现了现代主义格子的概念,它是一种无源头的复制系统。因此,克劳斯认为对现代主义美学时间的主要媒介来说,其产生条件不是来自于原创性/重复性这对术语,而是来自量产相对于单一,复制相对于唯一,虚假相对于真实,复制相对于源头。但在这些范畴中,现代主义往往要压制前者这些所谓的负面因素。在这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和前卫与原创的微妙关系了。从格子的原创到无源头的复制系统,原创其实就是博物馆、历史学家和艺术制作者的共同操作的产物。因此,整个十九世纪中,所有这些体系集结一起共同去寻找和保证对源头的权威性。这里,克劳斯用自己的方法把艺术品、媒介、艺术生产对作品背后的主体和其在传统艺术史叙述中所呈现的意义进行了分析与质疑,这在《前卫》中的《前卫艺术的原创性》和《你真挚的朋友》尤为显现。格子显然是她站在艺术自治的美学高度上来解构现代主义的神话,从而导出了艺术品背后的本质所在。
到此,格子完全向我们敞开了她自身的现代主义神话,同时她也成了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
非形—后现代主义启示
如果说格子是克劳斯结构主义思想的精髓,是她揭开现代主义神话的媒介,那么非形则奠定了克劳斯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非形主要出现在《前卫艺术的原创性和后现代主义神话》中的《不再游戏》里,接着克劳斯在1986年春季的《十月》发表了《反视觉》,在1997年的《非形—使用者指南》中在1996年,克劳斯与耶维-阿伦·博瓦(Yve-Alain Bois)在巴黎由博瓦作为《非形:使用方法》的策展人,1997年,跟此次展览有关的书籍《非形—使用者指南》出版)。非形来自巴塔耶的思想操作。按照巴塔耶在《文献》(在《非形》导论中,博瓦阐释说,《文献》是巴塔耶的另类式追随人文主义的基地。比如,在这里,“夜莺”在传统的文本和各种媒介中,它象征着美好的东西,可以由玫瑰和乳房替代,但不可以由大腿来替代。而《文献》的主旨就在于挖掘夜莺不能被大腿替代的这种受压抑状态的工作,由此,《文献》一方面呈献了传统词汇能指跟所指之间的任意意指背后的受压抑状况,另一方面在揭开这层面纱的时候,在《文献》中引进了在媒介中并无任何寓意且被人们所忽略所遗忘所鄙视甚至所唾弃的那些词汇,比如爬虫、垃圾、唾液等) 的“词语条目”里所解释的“非形”(informe)的意思,哲学家的任务是确保每一样东西都有各自恰当的形状,有明确的界限与限制。但是有些词,包括informe,有相反的使命。它们的任务是打破分类,将哲学家松弛地覆盖在每样事物上的“数学长外衣”脱掉。因为“非形”对消解形状、合并差异敞开大门,它“得到的结论是这个世界像一只蜘蛛,或是一片唾沫”(Bois,Krauss5)。

Bois Yve-Alain and Rosalind Krauss - Formless: A User's Guide, book cover
在克劳斯的《不再游戏》中,她认为贾科梅蒂雕塑中有着昆虫头部的人是一种被更替的“非形”。头部本来应该是最高级的部分 - 思想、灵魂,却被更替成低级的东西,那些头部形象在超现实主义中用螳螂的变形来更替。贾科梅蒂非形的头部雕塑只能让人联想到巴塔耶的蜘蛛。有着昆虫头部的人,成为了无头人,当然这个词来自巴塔耶,在他的作品里,克劳斯认为,无头人犹如一个密码,通向概念的剧场,在那里,人类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无头人敞开了人类的一个垂直方向的经历—生命意义以及道德意义的提升--不过是指向否定的方向:向原始状态的倒退,一个向下的提升。这里,我们看到非纵向,即反纵向,这是巴塔耶的“下滑”概念。这也影响了贾科梅蒂,他重新定义雕塑,他的作品的结构反映出概念的颠倒的影响,显然,颠倒跟巴塔耶的反向更替或者横向有着本质的联系。
巴塔耶在艺术史的美学成名跟他对马奈的《奥林匹亚》的阐释有关。在巴塔耶看来,奥林匹亚是对神话奥林匹斯的否定。但是这并非因为马奈对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的嘲讽,也不是因为马奈画了裸女形象的妇人。如果奥林匹亚作品被认为属于一件不光彩的事件,那么是因为马奈用各种意识形态和形式符码来阐释裸体概念,比如把裸体放置在情欲的神话的或者现实主义的范畴中。对巴塔耶来说,马奈的奥林匹亚在于无根性,而这种无根性在克劳斯阐释贾科梅蒂的雕塑比如《通道工程》、《头部/风景》,以及诸如《回路》 和《不再游戏》中都属于典型案例,认为这些雕塑在形式上的创新,在于将垂直方向的轴心周转90度,从而使纵向的空间重叠在横向的空间上,这个革新在表现手法的历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也就是从雕塑在传统中的纵向转向横向,甚至把整个底座连根拔起,成为一个实体,底座与上部的实体正如画框与画像,针对这种无根性与横线转向,克劳斯考证了贾科梅蒂与巴塔耶详细的交往时间,认为贾科梅蒂受到巴塔耶《文献》思想的影响。而在贾科梅蒂转向纵向雕塑之后,克劳斯认为只有贾科梅蒂的那些横向雕塑成就了这位艺术家的伟大。

Photograph of Alberto Giacometti, by Cartier Bresson
无根对巴塔耶来说就是“根除”也就是连根拔起,巴塔耶称它为“下滑”,并认为下滑是马奈的秘方,下滑总会让观者预期失望,这就表明马奈产生的画面与当时视觉惯例是相悖的。所以,巴塔耶认为马奈的图像革命在于一种操作,相应地,巴塔耶也通过阐释马奈图像为媒介阐释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因为对巴塔耶来说,他要做的是用操作来替代传统上的形式和内容。按照巴塔耶的说法,在他阐释马奈作品时候说:“要打破主体,然后用新的基点来重新构建,这种做法并非要忽略主体;因此在献祭中,可以随意对待主体,甚至毁灭掉主体,但并不是说我们忽略了主体”((qtd. in Bois, Krauss 21)。 巴塔耶接着阐述,画家们不再侧重于主体与含义,这里,用另一面(随意对待,毁灭)来超越他们,来替代/更替(alteration)原先或传统上的面对艺术品/祭品时的传统阅读思维。在这点上,克劳斯在《不再游戏》中就用巴塔耶的献祭和替代/更替去与贾科梅蒂的30年代的雕塑作品对话。
但在《不再游戏》中,我们看到的是更替的结果:非形。由于更替本身包含两个不同的含义:分解与进化,因此在巴塔耶看来,更替既指代尸体的分解过程,也指代达到完全异质状态的过程,即神圣状态。巴塔耶用更替来描述人类自我表现的主要动机,这个词因此同时指代向上和向下的概念。这种双重性对于与尼采有着相近的哲学的巴塔耶,犹如至宝。于是,相应地,高与低,底座与圣坛两个极端的概念被保留下来。于是克劳斯指出,“正是因为概念矛盾的游戏,使我们可以思考巴塔耶长期以来乐于阐述的一个事实:自从有历史以来,暴力就存在于神圣的中心;为了达到真实,创造性的思索也必须同时是一次死亡的经历;任何有真实深度的时刻,如果缺乏同样深度的残酷,是不可能存在的”(Krauss 54)。
以更替的概念为基础,其双重性使得该词的能指在两极之间不断地来回摆动。《悬浮的球体》正是把同样的语意的摆动加入了雕塑当中,但是在克劳斯严密的分析中,这里,虽然这个作品的结构是二元对立,将男与女两个性别放在一起对比,但是两个性别的身份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男女之间的身份一直处于向两端滑动状态。那么对克劳斯来说,在一个性别指向来回摆动不确定的作品中,加入“第三性”是必须的。这里,克劳斯的“第三性”概念已经超越了结构中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第三方因素的引入与思考在这里可以初见端倪,在二元辩证中加入三元辩证在克劳斯后来对安迪· 瓦霍尔(Andy Warhol)的文章中已经完全成为成熟的思想了( “Carnal Knowledge”111-118)。
如果说更替成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是两极的再现,但更替本身并不意味着二元论,更替是一种行为,是巴塔耶思想中强调事物的延续状体,这与腐烂处于同一个范畴。那么非形虽然在《不再游戏》中只是一个更替后的再现表象。显然,克劳斯并没有去深究非形理论,只是把其作为与巴塔耶更替相关的现象。更替成为克劳斯在《不再游戏》的结构语言学的媒介叙述,成为一种操作。然而,与非形相比,由于更替本身所具有的概念实体性,也就是在二元中操作,从二元中,巴塔耶向人们展示了惯常中的另一极,正如巴塔耶在分析献祭时说,血腥的杀戮行为却具有欢快的特征。而对贾科梅蒂来说,如果纵向转向横向是一个更替,那么,对于巴塔耶的非形来说,其意指超越了更替的二元,是一个操作。这正如克劳斯在《不再游戏》分析中也指出,“非形”指代的就是“更替”制造出来的结果:压缩意义和价值。但非形不是通过对比,因为后者属于辩证法,而是通过腐化,腐化能刺穿词语周围的限制,使它降到与腐化物同质。于是,非形在敞开的同时又指向颠覆。
正是这种更替是克劳斯与博瓦要在非形展览中着力去尝试的,在这里,克劳斯与博瓦明确指出,非形首先不是一种主题,一种实质,一种概念。它是参与巴塔耶的粪便学和异质学的运动。因此,非形的颠覆性质对克劳斯和博瓦来说展示了巴塔耶的精髓。在非形展览中,克劳斯和博瓦认为,现代主义本体论要求艺术品有始有终,要求所有透明的无序必须被重新吸纳。因为它建立在假定和排除这对现代主义神话思维之上,后者共同协力把现代主义息息相关的东西调整成一种阐释性的格子。这就不难理解克劳斯与博瓦以非形为名,用水平(Horizontality)、低贱物质(Base Material)、悸动(Pulse)、熵(Entropy)来回应现代主义的论调。而《非形》中的垂直——纵向概念在《不再游戏》中已经被作为美学概念被克劳斯所阐释。在巴塔耶构想的解剖地形里,纵向的轴线象征着人类对于崇高、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追求。但巴塔耶认为,低矮的存在(在令人压抑的垂直假设的后面)才是力比多能量的真正来源。这里的“低矮”既是轴线,也是方向,代表真实的泥土的水平指向。如果说脚是引起激烈反应的部分,巴塔耶坚持“大脚趾”,因为脚同时聚焦了反感和爱意,它们是身体陷在泥地里的那个部分。

Rosalind Krauss -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MIT Press), book cover
克劳斯在《非形》中所谈及的批评思想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哲学精神,正如她在《不再游戏》中诉诸巴塔耶的各种术语概念和词汇去阅读雕塑,比如献祭、祭品、狂欢仪式、大脚趾、腐烂、唾液、向上、向下等等。在《非形》中,克劳斯阐释了非形展开的各种概念,并且在末章《非形的命运》中,克劳斯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去进一步解读非形的哲学思想,并且用卑贱(abjection)作为非形的一种表现方式来阐释。在文章中,克劳斯通过与巴塔耶、克里斯蒂瓦、萨特、劳拉·穆尔维对话,通过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来分析卑贱概念。当然,克劳斯在与其他思想家对话的时候主要在解读巴塔耶的非形与卑贱理论,她通过当时艺术家流行的对所谓卑贱的展览,通过克里斯蒂瓦对主客体的关系、恐惧概念等与巴塔耶的比较,以及通过萨特对主体自治概念的阐释,最后,克劳斯把卑贱定位在一种无区别的母性机理上,一种女性的崇高,尽管她由身体中丑陋的无穷的不可言说的东西组成,比如经血、排泄物、粘体薄膜等这些铸就了所谓的卑贱艺术,从而从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角度来分析巴塔耶的卑贱理论,进一步,克劳斯通过分析巴塔耶的吸纳、排除、异质(偏离)的探讨,从而回到对非形的命运阐释,认为由非形引发的水平、低贱物质、悸动、熵并没有被同化进当前艺术界理解的所谓卑贱,而且“我们的非形在于有它自身的继承与执行,有它自身的命运 – 它一部分参与了把我们从语义学和数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对此,卑贱艺术似乎完全被其束缚,本展览只是继续进行中的一章而已”(Bois, Krauss 252)。由此,在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在哲学艺术批评中行进的克劳斯。
本文原刊载于《文艺理论研究》
2017年第1期
文 | 周文姬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影视艺术系讲师
作者往期文章推荐
行进中的学术性翻译--关于《前卫原创与其他现代主义神话》的翻译随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Bois Yve-Alain, and Rosalind Krauss. Formless:A User’s Guide. The MIT Press, 1997.
[2] Carrier David. Rosalind Krauss and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rt Criticism. 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2.
[3] 何桂彦:“后形式主义批评与现代主义神话的破灭—罗莎琳·克劳斯对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的批
判”,《中国美术馆》12(2010):115-120。
[4] Krauss Rosalind,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The MIT
Press,1986.
[5] Krauss Rosalind. “Carnal Knowledge.”October Files. The MIT Press,2001.111-118.
[6] 沈语冰:艺术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7] 沈语冰、陶铮:“图像与反叙事侵入--罗莎琳·克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
(2015):17-24。
[8] 陶铮:论罗莎琳·克劳斯结构主义时期的艺术批评,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周文姬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