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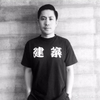
2018-10-31 23:05

倪有鱼
倪有鱼,1984年生,现工作生活于上海和柏林。2017年底,我们约定在他上海北郊的工作室见面。这里不是艺术园区,而是他常年隐遁工作的处所。随着他现在逐渐把一部分工作和生活转移到欧洲,使得他更加淡出于艺术圈的交际场合。四年前,倪有鱼获得了“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的“最佳年轻艺术家奖”。谈及此事,他显得很淡然,他很感慨CCAA奖的评审委员会竟能花费如此巨大的耐心去深入全面地了解他的工作系统和细节。虽然现在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但外界对他日常工作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
倪有鱼几乎每天工作,算是圈内比较著名的“工作狂”。对此,他不置可否,他戏称这只是一种“强迫症”。在这个充斥着聪明人的圈内,“工作狂”和“笨蛋”有时候差不多是同义词。在当代艺术越来越趋向“观念”之时,这种勤勉意味着他更笃信艺术在日常的劳作中所凝结的哲学意义。无论是利用水流冲击描绘的大幅风景画,还是在砸平的硬币上描摹极其微小的山水画;无论是用粉笔灰一点点精确拷贝的宇宙星空,还是凭感觉一点点刻画的虚假的刻度尺,倪有鱼在各种维度和材料的转换中无时无刻所强调的“手感”,使得他的艺术充斥着敏感的细节,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逆反于流行的气质。对他而言,艺术家的手不止承担塑形功能,那些由人体末梢神经决定的细枝的累积亦可被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道成肉身——当且仅当他将自身作为艺术的媒介与准绳时,其表达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生命力持久的“人造物”。倪有鱼告诉我:“相比锐器,我更喜欢钝器”。这令我想起阿伦特所谓现代之不朽(immortality)与古典之永恒(eternity)的对抗。
与此同时,如果在艺术中也存在“火焰”与“晶体”的区分,那么倪有鱼一定更趋向追求后者。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绘画方面的修习使他偏爱节制胜于直放,偏爱隐晦胜于坦白;另一方面,源自建筑、天文、哲学、几何学等学科的影响,他始终热衷为无逻辑的感受、无秩序的想象搭建空间,并且试图精准地通过这个空间的营造平衡、汇合与适应一切可言說和不可言说的总体。
ArtWorld:你的艺术起点是中国传统绘画,这个起点对你意味着什么?
倪有鱼:我在创作上有几个特点可能和我以前学传统中国画有关。第一,我的绘画几乎不借助照片,基本上靠记忆来描绘,哪怕是看起来写实的图像。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这样,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照着画”,默写成了一种习惯。后来读美院,才知道中国古代美术史中很多大师都具备非常惊人的天赋,他们通过长期观察和记忆完成了诸如《韩熙载夜宴图》甚至《清明上河图》这样伟大的作品。
第二,我的绘画基本上都是采用局部画法。这大概是因为我没学过“正宗的油画”。通常,传统的西洋绘画是整体铺完,再逐层深入,一步步细化。而我是从一个角落开始,慢慢“长”出一幅画来。这种局部画法也和中国传统绘画的方法有关。它的难点是,你要对整张画胸有成竹;它的好处是,画家会因此更专注细节。局部画法就像纸上散步,你会对每一笔的发展更敏感。
ArtWorld:在我看来,你的作品中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基于“临摹”的再创造,比如你在《瀑布与暴布》或《溪山》(一枚硬币上的微型绘画)里面画的山水;一种是基于“挪用”的再创造,比如你在《画院碑》或《摘星楼》里对图像的直接使用。你自己怎么思考“临摹”与“挪用”这两件事情?
倪有鱼:我首先要更正一点细节。《瀑布与瀑布》并非来源于美术史上的任何一个经典图像,“瀑布与暴布”是自己临摹并篡改自己的一张画,即先画了一张“瀑布”,然后再用相同的构图完成了另一张“暴布”。这几年,我深深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众艺术家。牛顿说:“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作为科学家的牛顿说得很好,但作为艺术家的我却不相信。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并不可能真正站在王羲之、达芬奇和董其昌的肩膀上。我们只是生命的个体,在艺术上我们都是从0开始的。所有号称的“创新”在我看来都是幼稚的妄言,反正我是不信的。
另外,我不认为艺术家一定是所谓的“创造者”。从古至今我们究竟创造了什么?其实从哲学层面而言,艺术仅仅是以不同的形式在不断转世投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系列叫“历史观”,我常常把历史比喻成一片森林,我们每往后退一步,观看的视野就大一点(艺术家按:自唐宋元明清,我们越往后视野越开阔),而最远处的树木却变得更模糊。我常常妄想我和先人的对话,所谓“临摹”和“挪用”就是一种小俱乐部里面的游戏,大家一起玩一种游戏,看谁玩得好。
ArtWorld:你不认为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明创造?
倪有鱼:对,我并不相信这些。
ArtWorld:你在装置中常常使用从世界各地的跳蚤市场收集来的旧物。为什么要使用旧物?使用现成品创作的艺术家不少,例如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
倪有鱼:是的,我非常喜欢约瑟夫·康奈尔!很多人说我做的东西和他很像,我从不避讳这种相似。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可以穿越时代,我最想和谁一起工作?我毫不犹豫就说了康奈尔。他很吃惊,以为答案会是一些更有名的大师。我说我是真地希望和康奈尔一起工作,做他的助手。每个周末和他一起去纽约25街的车库跳蚤市场,一起去甄别那些被人们忽略的东西,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同样有意思的是,他基本上不混在艺术圈中。
事实上,真正懂得康奈尔的人就会知道,他的艺术是根本不可效仿的。不可效仿,只能对话。做这类的东西必须依靠一种天性。你对于时间的理解,你对于“物”的观看之道,甚至是凭借某种癖好。这不是一类可以设计或是可以计划的作品,也不是技法的问题。使用什么样的材料在这里更是毫不重要。所以我在知道康奈尔之前的五年就这样做了,知道他之后的五年我还是这样做。我更愿意把这看作两个癖好接近的人的某种跨时代的对话,它一定是很平等的。
ArtWorld:从2010年开始,你就开始创作《尘埃》系列,这个系列是如何制作的?
倪有鱼:这个系列到现在已经做了八年了,每一件《尘埃》都源于一张星空的原图。比如18-19世纪出版的百科全书中的天文学版画,比如NASA的宇宙图片,还比如德国观念艺术家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的星空摄影作品。尽管来源不一,但这些关于宇宙的图像对于我而言都没有附加值,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将它们转述出来。这个过程中,我不能借助机器(比如投影仪)等任何科技手段,而是以最古典的方式,通过打格子将图像等比例放大,尽可能精确地手工定位每一颗星以及每一片星云,最后反复喷胶固定这些粉笔灰。这种漫长而重复的过程非常单调,很像田间耕作,也像和尚敲木鱼,最终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领悟一点东西。
ArtWorld:有时,艺术家所使用的媒介会成为他手的延伸。你在做水冲画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精力,使之完全受控?
倪有鱼:作为一个艺术家,大都希望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具有非常强的控制力,让作品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后来慢慢发现,水冲绘画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控制与不可控之间。这是一种拉锯,水流一方面是我的手的延伸,一方面我又不可能那么精确地控制它。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推敲完善这一整套的技法,包括水压、水量,颜料的干燥程度、冲击的角度,等等。很多人对这个过程很好奇,一张看起来安静的绘画,其实具有隐性的暴力。他们不知道如果所需的水量巨大,泼洒,冲击,那场面就具有某种疯狂的行动性。
ArtWorld:在你的水冲画中,线条很重要,看上去基本以黑色为主,很具象又很抽象。你对这些线条是怎么考虑的?
倪有鱼:我常常觉得在借助媒体观看艺术的时代,有一类艺术家会比较“吃亏”。因为有的作品基本上可以不看原作,而有的作品必须看原作。不但必须看到原作,在不同的观看距离里你所接收的信息也完全不同。我的水冲画可能算是这样一类绘画。这些线迹,在三米外看和凑到跟前看是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很多人看图片还以为我在油画布上画中国画,看了原作才理解我前面说到的那种“隐性的暴力”,更接近于表现主义绘画。
ArtWorld: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你做水冲画那么大的画幅的作品时,往往只画一个局部的风景。但在硬币系列中,你反而会构筑一个整体,为什么会这么去做?
倪有鱼: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在创作上我常常喜欢反其道而行之,这里面没有“应该”或者“不应该”。最早决定尝试在砸平的钱币上画画,只有2厘米左右,觉得很不可能,慢慢就画进去了。从一个苹果到一棵树,到一个局部的风景,再到完整的山水,再到勾草点苔,不借助放大镜,十年来硬币仿佛在逐渐变大,和古人练习射箭的故事差不多。事实上,现在整个艺术领域极小的作品很少,就好像在一个越来越趋于公共展示的年代,私密“把玩”的心态就很边缘了。
作者:子七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