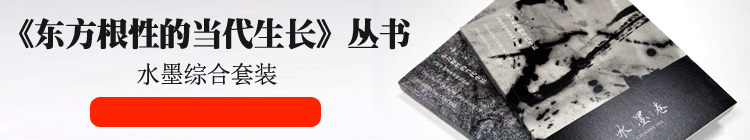2018年跟随雕塑家Alessandra Porfifidia于罗马国立美院学习
库:你年龄挺小的,为什么会关注一些感觉很严肃甚至有点沉重的主题?杨:这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一路走来也遇到了很多事,就对无论是美好的还是痛感的事情变得很敏感。库:你以前在天津美院学习雕塑,为什么会决定中途转到意大利留学?杨:我大二暑假和同学去欧洲玩,在意大利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还看到了美术馆中的贫穷艺术作品。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说要不要报考佛罗伦萨美院,然后就这样去干了。库:你最初去意大利想学习什么?意大利真正对你艺术的最大影响是什么?杨:当时想学习的是雕塑和装置这一部分。真正的转变是意识上的,从一种非自主状态变为一种自主状态。因为意大利的美术学院基本处于放养状态,教授不会对学生提什么教学要求,而是会提供无论是书籍、知识还是展览机会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和营养,然后一次次在展览中去磨练和消化这些东西。库:从你个人感受来说,意大利和中国的美院教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杨:最大的区别就是自主与否。对我来说,没有完美的教学系统,各有利弊。国内的学生还是挺幸福的,方方面面被照顾的很周到,在意大利的学生就需要事事亲力亲为,没有人给你组织什么,完全是一种野生状态。库:我知道你受到贫穷艺术很大影响,也非常喜欢马列维奇。这是为什么?杨:这其实是有前后逻辑关系的一条线索。我最初也是从图像上被吸引,当我去深入追溯的时候,发现我的出发点是不对的,应该从无论是历史、宗教或哲学的源头去重新梳理,不站在现场去观看和感受是很难真正理解的。贫穷艺术带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材料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把这一点辐射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我重新理解人与艺术影响很大。马列维奇对我而言,他在作品图像上的美感远逊于他的艺术哲学上的深度。他自己也说,他的绘画无法完全诠释至上主义,是有局限的,是会被符号化的。对于理解他的作品,要认识到他对之前的宗教、文化语境的颠覆性意义,如果不知道他所对抗的是什么,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马列维奇是二十世纪艺术的标志。最后我转向了对个体切身经验的强调,这是一种亲力亲为的方式。它不同于从文本或图像上获取信息的方式,而是伴随着五感的激活停留的更深。消失的,留下的——杨哲铭、王汉雯双个展现场
798瀚艺术空间
库:这次瀚艺术空间的展览也展出了你的绘画作品。贫穷艺术和至上主义大多还是以非具象为主,为什么你的画作仍是具象的?杨:我从小就开始在少年宫学画,等到系统的学习了具象写实的方法之后,我已经无法再完全拒绝它,抬手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用了很多圣像画中的姿势和手势,有一点像矫饰主义的风格但还不一样,我努力把形象简单化,甚至消散掉。我很难单独解释这些绘画,是创作装置之后的“余震”驱使我画了这些画,其中的观念指向性并不像装置那么明确。库:看你的作品,很多都与“身体”、“消失”有关,你害怕死亡吗?杨:每个人都会害怕吧。之前会想到这些,但现在不会了。经历了一些事之后,我觉得疼痛、欢欣甚至平淡度日等这些体验都非常重要,我觉得曾经折断的灵魂就像骨骼一样,在痊愈后会变得更加强壮。库:在2020年“未来已来——青年海归艺术家提名计划”中,你的作品被谭平老师提名并最终获得大奖。这对你的信心上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杨:肯定是有的,能被谭老师提名是我的荣幸。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能得到谭老师这样的艺术家的认可,是一件挺梦幻的事情。我也可以告诉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库:我知道在《库艺术》“朱金石创研工作坊”中,朱金石老师也一直给你和汉雯提了很多宝贵建议,对你们的创作有哪些影响?杨:朱老师对我们的帮助不仅局限于这一次展览,无论是从创作还是其他方面的建议和指引,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产生影响。杨:朱老师告诉我不要着急,做装置需要慢慢沉淀。以生命和肉身体验为主的艺术创作都需要去慢慢沉淀。毕竟,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艺术家去谈生死,连我自己甚至都是说服不了的,我现在做的只是针对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体验,还需要时间去慢慢延展。We can’t last forever Symbiosis杨:接下来还是以装置为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去画画,认为系统的写实训练对我是一种束缚,甚至花了五到六年的时间希望把这些忘掉。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淀之后,它转化了,就像反刍一样感觉又回来了,我想所有的经历都不会白白浪费,我想重拾绘画,但一定不会是完全具象的,也不是完全架上的,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呈现。We can’t last forever Symbiosis
消失的,留下的-杨哲铭、王汉雯双个展
正在798瀚艺术空间展出中



长按二维码或“阅读原文”
了解并参加工作坊
作者:库艺术KUART
特别声明:本文为艺术头条自媒体平台“艺术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艺术头条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