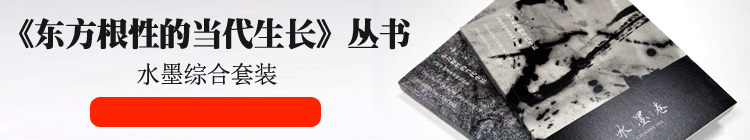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打破了人们寻常往复的生活,社会的车轮被迫戛然而止,接下来便是一段漫长的“自我隔离”……时间不再奢侈,反而显得有点难以填满。习惯了酬应热络的我们,如何学会静下来与自己相处?在生命面前,艺术还有何意义?此时此刻,是否更加向往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自由?每日看着手机上更新的患病人数,还能否做到摒弃外物,拿起画笔,全身心的站在画布面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困境只会激发真正的艺术家更为澄明无我的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之中,何时何地都不会停止。正因生命脆弱,时光宝贵,才愈加不甘心将哪怕一丁点能量耗费在虚妄之中。灾难终将过去,无论曾经如何刻骨铭心,终将成为历史的一瞬。而对艺术家来说,绘画是一生的事业,是与内心和灵魂无休止的对话,是回向自心的孤独而漫长的道路。古语曰“文章必穷而后工”。背对外界的喧嚣,需要更加无我的专注和饱满的热情,这种精神力量也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蕴蓄于作品之中,成为作品光亮的一部分。绘画不止是反映灾难,也不限于直接讲述现实,绘画的意义和目标远大于此。绘画是艺术家的精神自传,我们无需语言,无需描述,只要去观看,其中存有着更大的信息。在每一个笔触,每一笔颜色中,去体味那些或复杂或单纯的属于绘画的快感和愉悦,它们如水般穿过命运的窄门向前流淌,永不停歇,这正是对生命的真实礼赞!
创作中的仇墨娇
2020年拍摄
看过很多人在网上留言说“2020年重启吧”,显然这侧面反映了大家对这个不寻常之年的真实感受。现实世界远比电影里的更“精彩”?如今看来,这样的观点还真是不能轻易否定。每次看到一些灾害类的新闻,如气候变暖又导致某一地区冰川解冻、北极熊被拍摄到在人类的垃圾箱周边觅食,或是某个地区出现了未知种类病毒,都会心生感叹。我曾思考过关于生命的很终极的问题,我认为那是无法回避的,即便你可能总也找不到一个有说服力的“解”。人类在地球上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依附于自然,自然需要我们?灾难电影所建构的虚幻世界已逐渐不再那么的“虚幻”了,有时候前辈们会感慨时代变化异常快,当我到了他们的年纪,生活的变化是否也会超乎我的想象?疫情之下,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让我将有关对“隔离”的引申思考转移到作品的形态上。于是,在这几个月以来的创作中,部分作品我尝试通过材料建立视觉的“隔离”,希望从中获取有异于传统绘画颜料所带来的体验,又或是在“完结”的画面上另辟蹊径,在画面的“破”与“立”之间徘徊。反观自己的作品发现,创作过程中不总是按照我的预期发展,还有一些不能完全说清甚至可能尚未察觉得到的状态。奥班恩(Desiderius Orban)在《艺术的涵义》中提到“绘画的支配”问题,“作画过程中作者失去了对画的控制”,是否可以说明绘画在某种时刻是可以操控创作者的呢?我作品里的某些部分是非典型、非预设的,“创作”本身所特有的不可言说性吸引着我持续探索。历史上有一些艺术家曾在回忆录里叙述他的最佳作品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时完成的,反过来想可否理解为刻意追求的事物更难以实现?我此时又联想起之前和一位敬重的老艺术家聊天时,他提到:如果一个人执意要成为“成功的艺术家”,那大概率做不成,尝试着去做一些别的领域的事情,再回过头来做艺术…绘画创作对外界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它不是所谓的“刚需”,然而在西方几个世纪以来有关绘画的复兴运动却是反反复复的。现如今是什么原因使得有相当数量的人依然坚持这样传统的、有限制的表达方式?于我而言,看重的是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独立思考、对经验保持怀疑的态度。疫情的突如其来,仿佛提醒着我们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外界从不停止对绘画的未来做出各种预测,但预测终归是预测。我意识到某些干预作为创作者需要尽可能去排除,以求更纯粹的、个体的视觉痕迹。创作间歇,遥望窗外,蓝天碧树、众鸟高飞的场景总是最能让人舒心。面对自然,我永远保持敬畏之心。库本科、硕士研究生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曾赴美国麻省美术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与实践。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获取收录艺术家仇墨娇的学术文献刊物

长按扫描二维码,享更多惊喜

作者:库艺术KUART
特别声明:本文为艺术头条自媒体平台“艺术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艺术头条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